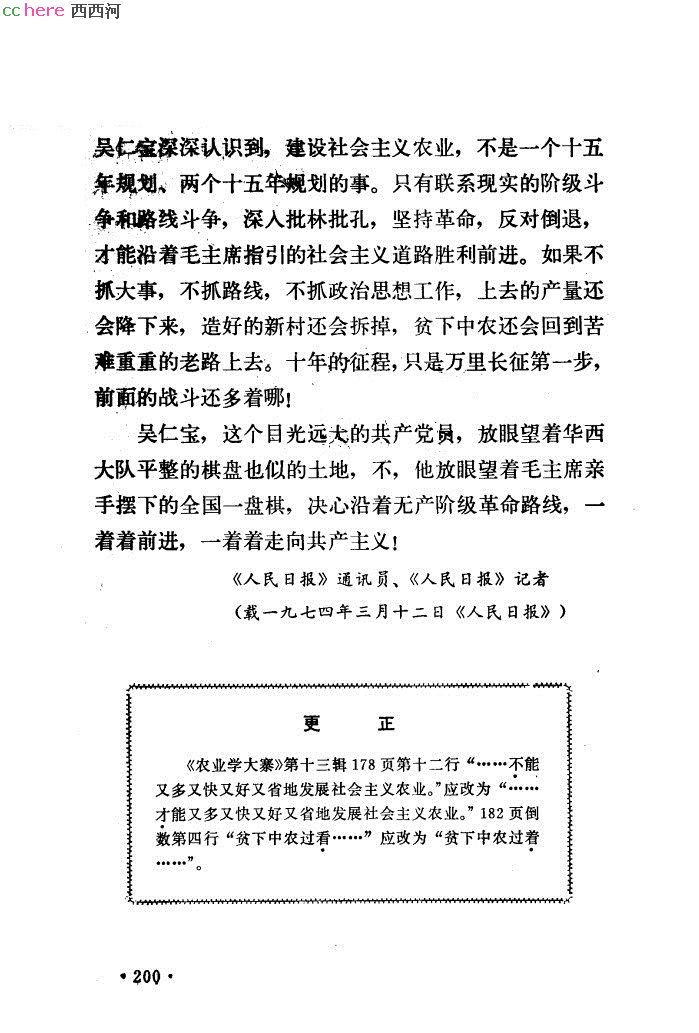主题:【文摘】特务村记事 -- 万年看客
http://www.chinaru.info/News/zhongetegao/25104.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1/08-30/3293249_4.shtml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hnjd/detail_2011_10/03/9634633_3.shtml
http://www.ims.sdu.edu.cn/info/1014/9319.htm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hnjd/detail_2011_10/03/9634633_0.shtml
凌晨三点多的宏疆村,朝霞的光辉已然可见。78岁的老汉徐维义已经出门,去江边收他昨日布下的渔网。虽然是夏季,这里的早晚温度也只有五六度。徐维义仍穿着冬季里的一身旧棉袄,拄一根老树棍做的手杖,因为文革遗留下来的严重的腰疼病,他的行动有些笨拙迟缓。
位于黑龙江黑河市逊克县车陆乡的宏疆村,低调地隐匿在雄鸡版图的“鸡嘴”附近,与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咫尺相望。村里人大多靠耕地、打渔或养猪为生,2010年一个小伙子因勤劳致富当选了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十佳青年”,被当地人视为值得敲锣打鼓庆贺的大事情。然而,在这个只有165户人家的小地方,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在内,大部分村民都有着深蓝色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和浓密的络腮胡。
宏疆村离县城几十公里,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徐维义捕鱼的这条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分界线。江的对岸,便是俄罗斯。徐维义说,他母亲的老家就在上游一百里的河对岸。中苏交恶的时候,江中小船受到严格管制,不能划过江心,晚上八点以后,船必须停靠在岸边。冬日,黑龙江冻上厚厚的冰,江中心便会被边防人员插上标志,沿江村民也会被告知不得越界。
徐维义长了一张典型的俄罗斯人脸孔,蓝眼睛,高鼻子,络腮胡,但他其实是俄罗斯母亲与闯关东的山东人所生的混血儿。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立引发难民潮,以及随后的大清洗运动等各种原因,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先后迁入中国黑龙江境内。早在沙俄统治时期,逊克县兵团村王金财的父亲就在对岸做生意。几年后,他跟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住在离中俄边境90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时期,也是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前期。为了保命,王金财的父亲赶着马爬犁,拉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回中国。
山东平度人苗平章在苏联做买卖时,娶了当地一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几年后,生了四个儿子。苗平章的儿子苗中林说,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江边的屯子,“中国人都喜欢在江边住,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回跑。苏联成立后,开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财产都得归公。大家一看吃亏啊,就拖家带口跑回来了。”到中国后,苗中林一家落户在了逊克县边疆村。“当时情况基本都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男人娶了苏联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个词,“捡洋落”。
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梅利霍夫给出的数字,在中国,俄侨人数最多时达40万人。20世纪20年代有10万人返回苏联,另有10万人离开中国去往美国。真正落地生根的多是与中国人组建起家庭的俄罗斯妇女。据俄罗斯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逊克县的县志记载,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县有无国籍外侨(他们多被苏联政府取消了国籍)205人,女性189人,占侨民总数的92.2%。
“苏联老太太”——徐维义的儿子们常常这么称呼他们的奶奶葛金丽娜。奶奶家族姓亚力山大,是俄罗斯贵族后裔。孩子们小的时候,家里常常能收到从河对岸邮过来的瓜子、糖和被面,这令他们如过节般欢喜。
【徐维义:那时候,那地方也就是挺荒乱的,闹这个闹那个的,也没法过日子了,完了说就跑到这边了,就上这边求个生活,就在这边就找个老头,就找我爹,干脆就生了我们这么一帮。】
当年,这个名叫葛金丽娜的贵族女人把1岁多的孩子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冰封的江面,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山村。她嫁给了一个闯关东的山东人,在宏疆村生下了七个孩子,徐维义是第一个儿子。
张玉福的父母都是第一代混血人,他的母亲就是徐维义的姐姐。虽然他当年年纪很小,却整日和村里的老太太在一起。
【张玉福:我问过,我说我的奶奶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他说她们几个年轻人,苏联人,就那么就过来了,过来了就在这边找对象就没回去,后来也挺后悔,后来那时候叫光复,来回就不那么随便了,不随便走了之后,她们就在这边生孩子了,后来也想,能不想吗,一下子两国,不像咱们邻居还能串串门,还能沟通一下子,写封信什么的,看一看,这一下子就回不去了,哎呀,有的时候,逢年过节她们就在一起喝酒、跳舞,跳完了就哭,这我都记得。】
【徐维义:她的习惯喝牛奶。穿裙子,人家那体格都好,穿裙子,冬天干脆也不穿棉裤,不像咱们穿的老棉裤,人家都穿单裤,穿的裙子,抗冻。喜欢喝酒,喝酒一般都是些个老太太,在一起跳,唱歌,就喜欢这个。】
【张玉福:开朗,她们一逢年过节都在一起跳舞,跳、唱那种,也没什么乐器,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也记得,我们在旁边,拾起那个盆呐什么东西,拿着筷子打着点,她们就跳,就蹦,就是她们的主要乐器就是口琴,还有手风琴,那些老太太也很多都会吹,“五一”前后,他们有一个节,苏联有一个很隆重的节,她们那时候必须碰到一起去,上坟、喝酒、跳舞这种习惯。】
徐维义的大儿子徐福胜尽管已经是俄罗斯移民的第三代,可还是长了张酷似俄罗斯人的脸———蓝灰色的眼睛、络腮胡子,硕大的鼻孔里甚至能塞进一个一元钱的硬币。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仍记得老太太喜欢穿蓬蓬裙,将他往裙子里一兜就可出门,方便得很。每次餐前,老太太都要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后再吃饭。“后来我说奶奶你老整那玩意干啥呀,她就不再比划了。”徐福胜今年50有余,跟他父亲一样嗜酒,生性粗豪。
“以前屯子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每个礼拜,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村民苗中林说。到后来屯子里的中国人嫌烦,就搬到了绊子场一带,这才有了现在的逊克县城。宏疆村的村民回忆说,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夏天,江面上有苏联的船驶过时,一些女孩子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气得直跺脚,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中国。
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日本警察队就驻在边疆村,除一名日本队长外,其余都是汉奸。“有人想往苏联跑,被抓住,给揍死了。”苗中林说,“最坏的就是那些‘二鬼子’(汉奸)。”
村民袁广荣的姑姑16岁时逃回了苏联,那一年,日军正占领着东北。“当时家里逼婚,非让我姑姑嫁给一个姓董的混血老头。成亲前一天,我姑姑跑去苏联了。一起去的还有我爷爷的‘团圆媳妇’(童养媳),那女的成天被我爷爷揍,就也跟着跑了。”上世纪90年代,袁广荣的姑姑到中国寻亲。袁广荣这才得知,姑姑刚到苏联,就被当地警方抓住,以为是对岸驻守的日军派去的特务。蹲了两年大狱后,被送到莫斯科。前来寻亲的姑姑也听说,她走之后,父亲发现自家闺女跑了,赶紧报告了警察局,结果被日本警察当成苏联特务,活埋了。
与苏联人的关系在和平时期并无影响。因为是外国人,在新中国的政策下,他们虽没有户口,土地改革等运动中也不曾被亏待。在文革之前,苏联老太太们还常常得到苏联亲人的照顾。
【徐维义:还有那个照顾呢,照顾是那时候粮食不缺吗,给大米,一个月给几斤大米,给豆油,就是好比是咱们三两豆油吧,另外给她三两,多给三两油,大米根本就没有给的,就她另外给几斤大米。邮的被面,烟,就是一些浮皮潦草的,就是这个胰子、手巾、就是眼前这些个东西,烟,乱七八糟的,就邮些这些东西,完了说你要接到,马上给我们写信,我们很好很好的东西给你邮来,这文化大革命就完了。】
中苏友好,江两岸的人来去自如,互通有无。苗中林跟母亲学过唱苏联歌,跳苏联舞。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进了部队文工团,在朝鲜待了三年。如今80多岁了,苗中林还记得些舞步,兴起时,两只脚轻巧地挪着小碎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会做些列巴花,现在断了,没人会做了,全都断了。”
196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两岸关系变得紧张。村里曾经有人去河对岸做生意、探亲,但边境在一夜之间被封锁,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村里。徐维义说后来没等到很好很好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1966年的一天,他接到通知,不能去江边打渔了。
【徐维义:打渔,别人可以,我就不行,不让我打,人不都是一样的人,那时候没有考虑这个苏联怎么怎么的,没有考虑文化大革命,后来我把网,冬天下网有这串绳,串绳搁里头了,搁里头了,后来就下去把那个网穿上了,那也不让你随便到那去遛网去,你不能乱说乱动,能让你随便走吗,完了晚间偷着去遛网去,那家伙鱼也多,都弄到大的鲤子、螯,净好鱼,得好几百斤,我忙活了一宿,自己。】
年轻的徐维义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其时整个宏疆村三十来户人家,只有四户属于纯正的中国人,其他都是中俄混血家族。最大的四个混血家族,即徐维义家、张运山家、徐英杰家和袁吉先家,都没能逃过这一劫。
文革时期,车陆公社(今车陆乡)制造出了一起“苏修特务集团”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务之多,使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苏修特务村”。徐氏家族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有7人:大哥徐维义、二哥徐维新、小弟徐维祥、大姐夫张运山、二姐徐桂贤和二姐夫王海丰,还有“傻大爷”。当年葛金丽娜将自己带来的儿子改名徐维刚,“户籍证明”上小男孩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长大成人之后,村里人都称他“傻大爷”。因为没有国籍,“傻大爷”反而因祸得福,没怎么吃苦头。“只是拿绳子将他绑在树上,没怎么打他。”徐福胜回忆。他的父亲徐维义则被关进了牛马棚达5个月。
当年徐维义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在徐福胜眼里,父亲特别能干。闲暇时,常常上山打野味。“我家的伙食是村里开得最好的。我爸常问我们:想吃水獭吗?想吃他就去打。”打来的野味也可拿去卖钱。一只黄鼠狼是九块二毛一。而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最多也就10来个工分,只够买支冰棍。
徐维义被关牛棚后,徐福胜负责给父亲送饭。那时他13岁,读小学五年级,每天早上4点起床,走三里地去送饭,一日三次。造反派们逼徐维义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为自己发明了一条罪名——“上山搞资本主义”。
【徐维义:就是变相体罚你,撅着,脑瓜子快拄地了,我撅了七天七宿,差不点儿没撅死,眼珠子都要控出来了,换着班,七天七宿,什么人能架得住呀,眼看就要行凶。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抡,打趴下三个两个还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让我歇下来。我就那什么了,寻短见了,后来又一寻思,这上有老,下有小,我死了,他们不就完了,寻思寻思拉倒了,别那啥了。还有几回,整得严重了,走、跑,大江,水,凫水,我水性挺好,我寻思干脆走了,你走,走也是不行,还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呢,那不更麻烦了吗,挺着吧,爱咋的咋的吧。】
【徐维义:就后院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行振,问他电台是什么样的,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样的,完了说是,就像茶壶似的,说是就是一样,就是没有嘴,那不就告诉你了吗,根本就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嘴说话呀。】
【徐维义:叫我交代在苏联那边整的枪,说把枪弄哪去了,说整下道杆村去了,整下道杆弄哪去了,给我哥哥了,就往自己家的人身上整,你还能整到别人身上,根本没有的玩意儿,那家伙,让我去对证去,那是我二哥,这家伙,我哥哥急了,两个人对证,那玩意儿没有的事儿,那是胡说八道,他急眼了,摸起老板凳就……】
徐英杰今年74岁,同徐维义一样,是村里所剩无几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儿。他记得,妻子张凤云被关进牛马棚时是夏天,天气闷热,整个村子也极沉闷。 “在路上碰见熟人都不敢聊天,小心又小心,生怕‘人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每天提心吊胆,不知哪天就被抓进去了。”妻子被抓时,小女儿才刚刚满月,大女儿徐月娥每天抱着妹妹去牛马棚,让母亲喂奶,再抱回来。徐月娥印象深刻的是,牛马棚里关了许多人,用木板隔开,像牲口一样,互相不许讲话。
【徐英杰:问跟谁联系,怎么联系的,咱上哪说呢,咱根本没联系,你不瞎说吗,你还就得瞎说,你不瞎说不行,不瞎说他揍你。他给你安排说是,他不知道从拿调出来的,他说,联系的时候,说这个电棒,手电筒打三下,完了过去,到那块怎么怎么说,没有的事,根本没有这个事,你怎么安排呢。】
【徐维义:有一个姓潘的,是一个老跑腿子,那边有个河,在那河那地方放牛,完了说他是个特务,说特务你怎么联系的呢,说是,我实在什么玩意,搁那个火柴,一划火柴,那边就过来人了,那个火柴,那江那么宽,拿个火柴他能看见吗。】
【徐英杰:当时栽一颗树,给他砍了吧,特务家的树,给他砍了不要。特务家的孩子,小孩跟小孩那么说,小孩也不懂,揍他,他说特务家的孩子。劳动吧,生产队不是评单位分吗,评分,你干得再好,你也没人家那个好人评分多,你政治上不去,政治不好,劳动好,政治不好,应该评十分,我给你评八分,你就少两分。】
在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里,徐维义的大姐徐桂芝躺在炕上听人聊天。她蜷缩在那里,脸上木无表情,嘴角耷拉着。听到记者与他人聊天,提及文革,她从炕上起身,一言未发地离开了。“她本来话就不多,我公公文革中跳井死后,她的话就更少了。来了就往这儿一躺,不说话。”小卖部的掌柜、徐桂芝的大儿媳说。
徐桂芝的丈夫张运山是文革后县里唯一一个专门为之开了平反会的人。 在徐桂芝的二儿子张玉福的眼里,父亲能干,有见识,人缘好。“每天家里总有南来北往的客人,母亲炒菜,父亲和他们喝酒。”
年轻的张运山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当时村与村、村与县之间没有公路,为人热心、喜欢结交朋友的张运山自告奋勇承担起给供销社跑运输的任务。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妻子生病时,他能把逊克县唯一一台北京吉普车借来,带着妻子去医院看病。运动开始之后,张运山第一个被卷了进来,罪名是“苏修特务集团大头目”。据1979年县里给张运山平反的材料,他于1945至1947年给苏军当过情报员。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
【张玉福:最开始从社教开始,就说他有点历史问题,到文化大革命了,就把他揪起来了,就说“苏特”,“苏修特务”,那时候直接一个定论,就说“苏修特务”,觉得自己家哪能是“苏修特务”呢,是跟别长得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突然一个晚上好像是,就把我父亲叫去了,叫去搁那以后,第二天拿了一套行李,就在那就圈起来了,就给关押了,关押之后陆陆续续一家一家一家都有这个情况,就都给圈起来了。】
“我父亲被关在供销社大院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我每天给他送饭,但见不到他。我就整天骑自行车在那儿一圈一圈地转,只想看看他。”张玉福回忆说。
张运山被关进牛棚后,每天晚上都有造反派来光顾张家,房前屋后,掘地三尺。“若是情报员,家里必定藏了电台和坦克、枪支之类的武器吧,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找到。”最后全家人被驱逐到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里面只有一张炕。
“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开二哥的批斗会。我就在台下看着,我不想看都不行,必须得看。”张运山的妹妹张淑娟说。一提起文革,这个76岁的和善老太太就会不自觉地提高调门:“拿鞋底子、皮鞭、皮带抽他,完了让他爬回牛马棚。我实在不忍心看,又帮不了他。”后来,张淑娟自己也被关进牛马棚,落下严重的妇科病。
张玉福记得,父亲被打后,托人带话回来说口苦想吃糖。母亲将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块英国表卖了十几块钱,给父亲买了糖块。张玉福对造反派恨得咬牙切齿。批斗会结束后,他埋伏在路边,待造反派经过时,拿弹弓打他们,结果是自己被追打。
张运山作为“特务”头子,受到了最严酷的对待。当时只有10岁的张玉福获准给他送饭,见到了接受审查的父亲。
【张玉福:打嘛,打得受不了。那时候我记事,我给他送饭,送饭我就记得,身上都是血,满身都是血迹,那时候我小,也不敢吱声,送完饭就走了,他也不让看,大人去了不让,偶尔我送饭就能看看,打得受不了,自己可能是嘴里都挺苦,要糖块,我记得要糖块,我回去跟我妈说,我妈说没钱啊,我爸说实在没钱,把表卖了吧,有时候有那个鹦哥表什么的,他喜欢穿白的衣服,都是血,都是檩子,说起来跟渣滓洞出来审完了差不多,基本上都那样子,我听说他们都说身上打完不沾到衣服上了吗,完了就给撕下来,那你说那是不是酷刑嘛,他能受不得了吗。】
终于有一天,趁大家都去田里干活,只有一个年轻女造反派看着,张运山跳井身亡。
【张玉福:身体不行,打得走路都走不动了。
记者:就是你们看到?
张玉福:我们看到的时候,走路非常慢,走不动。他就是路过厕所,他想上厕所,他就是存心的,路过厕所,趁他不注意就跳下去了。捞起来,就这么草草地换衣服,我们也小,也靠不上前,草草地就做了个棺材,村里面出了个棺材好像是,很薄的一种木板钉一钉就埋了。】
那是1968年8月,张玉福12岁。他一直认为父亲个性刚强,之所以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张运山投井而亡,宏疆村“苏修特务集团”大案也不了了之。
1979年4月,县里来了平反工作小组,落实政策。一份平反材料显示,文革期间,百余人的上道干第二生产队(包括宏疆村和上道干村),有32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有12名社员被监督劳动。用张玉福的话说,只要家里有一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整个家庭就都被认为是苏修特务家庭,因此,村里约70%的人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
除了集体平反之外,工作组还专门为张运山召开了平反大会和追悼会。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张运山充当苏修情报员的这段历史早已清楚,不应作为政治历史问题。”开会的前几天,工作组派人来到张玉福家,给他做工作。
【张玉福:我跟我哥商量,我说咱们不行,就这么给平反,说两句话完事了,不行,我说平反咱们不能轻易就那么就罢休了,得让他们坐牢去呀,这给咱们整这样子,他们那时候都是违背政策了,可以这么说,那时候就比较懂了,我姑姑来说,我舅舅他们也说,做工作,算了,对我们家来讲,平反也没什么回报,拿我们那么多东西,作几个钱,不多,很少点钱。】
张运山平反的材料写,他于1945至1947年给苏军当过情报员。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张玉福说,这迟来的平反总算让大家心里都得到点安慰。
【张玉福:就是说我父亲有功,不是罪人,就是即使那封信送的也是为了共产党,为了红军,就是红军打日本嘛,这个是明确地讲了,这个我还记得清楚,因为你再小,你究竟是为什么把我父亲抓起来的,究竟你平反最后哪句话说的,对我父亲,你平反平的是什么东西,我能记住,我这个能记住。】
追悼会前,平反工作小组的人怕张淑娟在会场闹事,特地找到她,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就说,不是说我家里藏了坦克吗?你给我一个坦克镜子,行吗?”
文革之后,村中的苏联老太太也很少再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如今那一代人都已经陆续离去,葬在了宏疆村。
【徐维义:我挨整的时候,我说苏联那边,我跟我妈说,我说你苏联那边都没有男人了,我说你上这边来找个汉族人,我说你瞅瞅把我们整的,这是我跟我妈说的。我说苏联那边没有老爷们,我说你上边来找一个,给我们找个爹,生了我们这一帮,你瞅瞅给我们整的啥样,这是我说的。】
经历过文革的村里人对自己的外貌变得敏感。他们尤其憎恶别人叫他们“二毛子”,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最大侮辱,比骂他们的爹娘还严重。关于“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这种问题也被视为禁忌,他们习惯于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国家叫做“他们”。不少村民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儿子娶中国人,尽快了断自己俄罗斯民族的血统。
徐维义的孩子们都已结婚,和村里许多混血老人一样,他绝不允许孩子们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结合,希望后代们能在面貌上更接近标准的汉族人。
【徐维义:“二毛子”啊,我们也是不愿意听啊,跟人长的面目是两样,你非得说我们“二毛子”什么玩意儿,那不都是中国人嘛,我这些个儿子找对象,我说是干脆和我们一样的干脆不要,一个也不要,我四个儿子一个也没有混血人,有不少的要跟着的,干脆我说不行。不行。
记者:有过吗,谁和混血的,然后你不同意?
徐维义:有啊,我那三儿子,和那个老王家的,也是我们混血人,姓徐的,也是三姑娘,那是几姑娘我都忘了,干脆我说你找对象是对象,我说你爸这个事是干脆不允许,不同意。
徐维义:我那个小四儿(孙子),瞅着不比我的模样强多了吗?像我这个模样就不行,我出门啥的,人家就说,外国人。】
【袁吉先:我孩子不让他们混血。不跟他们混血。
记者:为什么?
袁吉先:我四个姑娘都嫁中国人。
记者:为什么?
袁吉先:有一次的经验还能。
记者:怎么叫有一次的经验?
袁吉先:这一次教训还不够,你都成了混血人了,以后你看他们,这都是两口子混血人,又生这么一个玩意儿,成天这样。】
经历了历史的动荡,尽管村子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边境旅游日益兴旺,这些混血人大多没有踏上过对岸的土地。甚至不愿再寻找血亲。
【徐英杰:公安局来问我,你找不找你的亲戚,要找我们帮你找。我说不找,找他没用,找他干啥呀。你找到这个亲戚能怎么地。今天来往明天来往,以后又成事儿。一会就够呛,伤老心了。以前一点跟人家联系都没有,给你安上罪名了,特务,离他们远点吧。】
“一次教训还不够?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徐福胜激动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1995年,徐福胜的弟弟徐福河娶了东北姑娘彭桂茹,生下了儿子徐然,举家欢庆。虽然徐然的相貌依然特别,但徐福胜坚信,只要一代代地坚持找纯种的中国人结婚生子,血统和容貌一定会变得“正常”些。平时的交谈中,徐福胜习惯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俄罗斯叫做“他们”。“他们俄罗斯的事我也关注啊,日本外长今天到俄罗斯去了。”话题一转,徐福胜又说到中国,“还是咱中国好啊,把农业税都给我们免了,嘎嘎的好。我们哥几个以后少喝点儿酒,多活几年,得看看咱们国家以后是啥样的。”偶尔喝高了的时候,徐福胜也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我们家是个大家族,纯正的俄罗斯族,你看我们这长相,黄头发、蓝眼睛。屯子里有的混血是茨冈族,黑头发、黑眼珠,相当于俄罗斯的吉普赛人,是受歧视的。”
如今,村里的混血儿已经到了第四代,从表面上看,大多数人的外貌特征已经“汉化”。不过,不少后代将事业拓展到了对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江对面的海兰泡打工、种地,不时给老人们带点儿黑列巴和俄式咖啡等特产。
曾经的“特务村”宏疆村如今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虽然在这里,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了。有些村民会用《喀秋莎》的调唱民歌,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四个萝卜剁吧剁吧,没有了花椒大料,倒点儿醋,酸不拉唧,你就喝了吧!”这首歌时常出现在村里的酒桌上。
现在村口的大门是花了三万元修建的。“罗斯民族村”几个大字十分醒目。“俄”字是前两年被徐维义和徐英杰捅下来的,他们的理由是“看了就有气”。省里领导来考察,想把村子的房子改建成俄罗斯式民居,老村长徐占杰带领村民们坚决反对。宏疆村村党支部书记袁新波说,尽管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但村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俄罗斯的民俗。“只是在1991年,给一些俄罗斯混血的村民发了侨眷证,考学时能加点儿分。”
现在,村子里的“中国人”和对岸的联系也断得差不多了。但是每月却有大量俄罗斯人从这里往返中国多次,带回廉价的牛仔裤、衬衫以及名为“阿迪多斯”的山寨运动鞋,他们甚至愿意坐上每小时一班的公共汽车到中国理发,为孩子购买玩具。侨民证在村子很吃香,徐维义早在1992年就办了侨民证,据说孙子考大学时能加20分。让村长徐占杰想不通的是,好些完全没有俄罗斯血统的山东支边人员都办上了,他这个“正宗混血儿”却办不上。最玩味的是,“国籍”一栏大多还标注着——“无国籍”。
“入乡随俗嘛,当年跑去俄罗斯的中国人也都改成当地习惯了。”附近兵团村的王金财说。由于从小跟着母亲学俄语,1992年,王金财到俄罗斯当翻译,一待就是16年。“我在那边碰到过一个中俄混血人,他爷爷是清末过去的。这个人就知道自己姓张,祖籍在山东,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还有一个姓苏的人,就因为有中国血统,1937年时被警察局抓去,人家让他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当时,这个姓苏的根本不敢露自己会说中国话。”
王金财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他在俄罗斯当翻译时,在一个汽车修理厂门口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夹着个公文包。得知王金财是中国人后,对方说,过去两国的争论都怨赫鲁晓夫。王金财客气地表示感谢,“现在想想,他能这么说,不容易啊。”王金财爱吃酸牛奶和酸面包,但妻子做不来酸面包,只得作罢。“要说俄罗斯的生活习惯,也就剩这些了。”
凭借酷似欧洲人的相貌,徐福胜当过几年特型演员。他引以为豪的就是走过不少地方,天津、宁波、舟山、东阳、横店都有他的足迹。上街买水果,小贩当徐福胜是老外,两块钱一斤的苹果,愣是跟他要15块钱一斤,徐福胜满口的东北话把小贩惊得懵了。
第二代中俄混血儿徐月娥是现任村妇女主任,也是县人大代表。1990年代她去北京开会时,有人问她是哪里人,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你既不是俄罗斯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国人。”她叮嘱长着一张俄罗斯面孔的女儿,“一定得嫁个中国人”。徐月娥认为,这是为下一代着想。“这几十年下来,总觉得会受歧视。就算家里两口子吵架,对方都会说,你个‘二毛子’如何如何。这话我们听够了,不想让后代再听了。”
张玉福后来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娶了上海女知青为妻。组织上曾力劝他入党,并许诺替他写好申请,只需要他签名。“但我没同意,因为我父亲的事情,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可我儿子就入党了!”张玉福语气里不无骄傲。张玉福的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今年74岁的张树娟提起文革岁月只会摇头苦笑。“说起来就像个笑话,可不就是个笑话吗?”那时候每家一个特务指标,只要承认了罪名就会少吃些苦头。但张树娟无论被关牛棚里多少天,还是咬牙否认,她觉得没有的事情不能承认。
徐维义如今已是村里最年长的一辈,颇得村里人尊敬。过去的许多事他已不愿多提。有时候在村里偶然遇到当年折磨他的造反派,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打个招呼。他的同母哥哥、如今88岁的“傻大爷”徐维刚则是宏疆村里所剩无几的拥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时间在他这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专门来看他时,侄子们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帮他换件像样的衣服,戴上顶脏兮兮的军帽。每到这时,徐维刚会挺直腰板,对着闪光灯露出婴儿般惊喜的笑,湛蓝色的眼睛泛着异常的光。傻大爷嗜酒,爱唱歌,常常一个人自编词曲,即兴高歌,若让他重唱一遍,他就懵了。虽然母语对他而言已经成为远去的记忆。偶尔,他会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用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那啥,我叫安德烈。”
“千万别问他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大侄子徐福胜警告,“谁问跟谁急。”
但我觉得应该多发一点,河里的多数人是喜欢宏大叙事,对于个体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绝望挣扎,不会太有感同身受。
现在仍然存在,而且会继续😨
极左得支持毛主席啊,假左不是,是曲解毛主席。
比如毛主席说宋彬彬叫宋要武,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他们就说毛主席要武斗,正常人谁会这么理解,进而出现了红八月血腥北京,大兴事件,这和毛主席有一毛钱关系啊?
要武斗,要暴力批斗黑五类,这些和毛主席有啥关系啊?没有啊。这不是极左,这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的假左。
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根本不遵守,极左是不会这么左的。
首先毛主席并不等于极左,所以极左与主席不能划等号。纵观主席的一生,他一直在与极左和极右作斗争,没有妥协过。
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中央”,简称“无限忠”。毛主席本人就提倡辩证法,我相信就是他本人也不希望人民群众采取无限忠的方式,这个就是极左的一种。诸如此类的事情极多,比如早请示晚汇报,极端个人崇拜,文字狱等等,当然有些方法方式左右是不分的如打砸抢,武斗等等。
说文革有极左派活动,并不影响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相反就是因为那些极端分子的捣乱才使得文革中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情,反倒是给主席脸上抹了黑。
然后加强中央的权威性,借以达到自己的权力目标。因为政治局他们亲苏派还是多数。
早请示晚汇报,我敢肯定是他搞的,因为停止就是他的名义处理的,当然毛主席反对。
文字狱我估计也是他搞的,应该不是老干的集体行动。肯定不是林彪搞的。
什么是极端化,就是做的过分了,比如批斗变成了暴力直接揍人,而这个是一开始就达到了高潮,然后被毛主席制止了的。
破四旧不仅进人抄家,揍人,还有啥都砸,这就是过分了。这也是联动老干的子弟和保皇派的杰作!
或者说思想极端化,比如抑制私有经济就消灭农村集市,等等吧,还有不让开五小工厂。毛主席则是支持华西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