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民族音乐点滴 -- 黄序
- 共: 💬 44 🌺 344
民族音乐这个范畴有点大,我先尝试从狭义的民乐起个头😏。
先说这个名称,除了大陆的“民乐”和台湾的“国乐”,实际上还有香港的“中乐”(香港中樂團)。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高下之分,各家当初都有自己的道理。
有意思的还有新加坡,我在那儿呆过几年,知道新加坡人的小九九,喜欢使用华族、华语这样的概念。相应的在音乐领域,他们的说法是“华乐”(新加坡华乐团)。
整个华人世界的叫法应该是很难统一了,也没必要。综合四方的各自表述,意外地得到了这样的合集:
中、华、民、国😂
广义的民族音乐应该有一个很宽的谱系。
在这个谱系的一头是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经典,包括宫廷古曲和文人雅乐,中华古韵有所谓十大古曲的说法,比如《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汉宫秋月》、《夕阳箫鼓/春江花月夜》、《平沙落雁》、《阳春白雪》等等。对,曲如其名,这些构成了谱系中阳春白雪的一端。当然经典不止十首,但对比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音乐遗产算不上特别丰富。而且这些古曲的原作者和原谱大多很难考证,有些已经可以认定是后世伪托古人所作。
谱系的另一头来自乡野和市井,包括各民族各区域的民歌小调,地方戏曲,宗教和世俗仪式音乐等等,构成了谱系中俗的一端。
以前读白居易《琵琶行》里“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诗句,心说他怎么一点没有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呢。
不过后来慢慢地觉得白老师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很多民间的音乐确实需要经过提炼和艺术加工,才能给听者更完美的体验。与此相关的创作填补了民族音乐谱系里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是今天大多数音乐爱好者更经常接触到的一部分。
这部分的曲目包括音乐家搜集整理加工的民歌民乐;根据民族音乐素材,使用中国传统作曲技巧谱曲,用民族乐器或民族唱法演绎的器乐和声乐,也有不少是把民族乐器的版本改编为西洋乐器版本,有些甚至就是直接为西洋乐器进行创作的;广义上说还应该包括基于特定的中式题材完全按西洋音乐的作曲和演奏技巧创作的作品。
这些创作有些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代表人物包括刘天华、聂耳冼星海、贺绿汀、任光、王洛宾等等,但是更多的作品是建国后前三十年当中问世的。
抄一段我以前的帖子:
建国后前三十年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整理和改造是空前的,也很有可能是绝后的。这里的原因,一方面是有政府层面文化部门的系统组织,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可以说既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又有主动深入民间的意愿;既有从民族音乐中汲取养分的谦卑态度,又有去芜存菁推陈出新的使命感;还有通过苏联老师学习借鉴的现代西方作曲理论和技巧,和作曲家群体本身扎实的工作作风。
当年李德伦还是谁讲起对民间音乐的再创作,要达到做中国的巴托克这种高度。这比现在只会给自己作品加民歌佐料和所谓原生态噱头的艺人,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土鳖扛铁牛~
就在这里凑合一下。
一般而言,大家的感觉里,除了古琴以外,中国的大部分乐器,或者音乐,相对比于西方乐器/音乐来说,显得比较土。比如二胡和小提琴,又比如唢呐和萨克斯风。说到唢呐,看过《百鸟朝凤》,里面关于唢呐的表现和演绎相当的不错,以至于我当时很有一种冲动想弄个唢呐来学学。
我总觉得很多中国音乐其实也还不错,但是发展突破很少,甚至传承都有问题。所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我觉得和乐器本身的精致程度,表演者的服装、气度,以及表演场所的豪华程度都有关系。民乐方面在这方面和西方音乐有非常大的差距。哪怕是同样好听的音乐,大家可能会愿意花高价钱去钢琴小提琴的音乐会,但未毕愿意花多少去听唢呐二胡的音乐会,因为档次体现不出来。更糟糕的是,因为档次体现不出来,能够在相应乐器上下功夫写好曲子的人和精力就不多,也就难以形成新的音乐补充,变成了死循环。
《牧童短笛》是贺绿汀先生30年代创作的一首“中国风味的钢琴作品”:
它由A-B-A三个段落构成,第一段使用了复调技法,注意表演者双手分别弹奏两个不同的独立行进的旋律,两个旋律互相对答呼应,另外相同乐句重复时也会注意力度变化,简单的旋律有了丰富的层次感。
第二段转为主调音乐,右手演奏带装饰音的旋律,左手则充当伴奏,跳跃起伏的音型表现了牧童活泼的情绪。
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再现,重新回到复调音乐中,但在一些乐句中又曾加了一些装饰音,重复中又有一些变化。
《牧童短笛》使用了西方音乐中复调与和声的作曲技法,但这类技法的使用又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完美表现了中国化的音乐之美。
支声复调是同一旋律多声部不同变体的展开行进,从而产生一种衬托的效果。这个手法倒是常见于欧洲以外地区的传统音乐当中。
很多年前我在印尼巴厘岛看当地的甘美兰音乐表演,两组乐手各自演奏同一旋律的不同变体,其中一组带有密集的装饰音。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敲击乐器,旋律性没那么强,如果不是主持人说明我都意识不到那是一种支声复调的风格。
其实我们身边的民族音乐有更简洁的例子:
视频开头诗朗诵过后的女声二重唱,仔细倾听可以分辨出两位歌手的歌声基于同一旋律却又略有不同,合二为一后产生了更丰富多彩的音乐效果。
这几天多位河友和我本人都先后提到歌曲《浏阳河》,以及王建中先生改编的钢琴曲。王老师的这个钢琴版里也用到了支声复调的技法:
引子部分可以听出来是歌曲的最后一句,然后用大段连音表现河水奔流的气息。接下来用主调音乐的形式第一次呈现浏阳河主题,右手旋律,左手伴奏。接下来请注意在这个主题第二次出现时(大约在视频1分11秒处),王老师使用了支声复调的手法,中音区的左手演奏简单的主旋律,而右手在高音区演奏的分支声部则是左手主题旋律的加花装饰,形成了多彩的织体,好似围绕主题绵绵不绝的华彩,在使音乐更加流畅丰富的同时也营造出一种浏阳河上波光粼粼的意象,令人美不胜收。
~土鳖扛铁牛~
我小时候有段时间莫名地喜欢笛子曲,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什么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但就是爱听,尤其是对广播里经常听到的几首印象非常深刻,其中之一是《小放牛》,后来知道改编和演奏者是民乐大师陆春龄。这个曲子虽然源自河北民歌,经陆老改编后倒是颇具浓郁的江南丝竹韵味。
陆老很长寿,晚年还留下了不少立体声录音,我非常喜欢的还有《鹧鸪天》、《欢乐歌》、《水乡新貌》,以及古意盎然的《梅花三弄》和《关山月》等等。
另外一首听起来特别爽的是北派笛子的新派代表作《扬鞭催马运粮忙》,众多演绎者当中,王铁锤这个名字实在是令人难忘。可惜现在找不到王版视频,贴一个俞逊发版:
与之齐名的是另一首新派曲目《牧民新歌》:
我后来自己开始买唱片的时候,比较活跃的笛子演奏家还有蒋国基、张维良等人,而俞逊发曾经跟随包括陆春龄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北派前辈笛子大师学艺,堪称同辈中的佼佼者,却意外地英年早逝,非常可惜。
印象当中第一次“看”到的演出,是邓世昌😏表演的《十面埋伏》。邓大人的琴声把刀光剑影危机四伏的紧张气氛和失意的水师管带忧郁愤懑的个人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很长时间我都以为给影片配琵琶的是刘德海,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刘的老师之一杨大钧。
之所以开始以为是刘德海,是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琵琶演奏家的代表人物。除了对传统曲目造诣颇深,他也参与创作了一些现代曲目,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吴祖强等人合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
同中国颇有渊源的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曾经数次访问中国,最早是个人前来指挥当时的中央乐团,演出曲目就包括刘德海担任独奏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同为吴祖强编曲的弦乐合奏版《二泉映月》。
演出之后第二天,小泽老师造访中央音乐学院,学校安排当时二胡专业的学生姜建华为他现场表演原版《二泉映月》,小泽老师听后感动到泪流满面,连说要是事先听了你的演奏我昨天就不敢上台指挥这首曲子了,他甚至认为这样的音乐只应跪下来倾听,说着说着就真的要跪下来,把陪同人员搞得不知所措。
多年以后小泽老师在又一次访华时和姜建华重逢,重现了当年那个小泽倾听小姜演奏《二泉映月》的场景:
79年中美建交后小泽老师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再次邀请刘德海和波交合作演出《草原英雄小姐妹》,演出录音后来由飞利浦公司发行了唱片:
虽然此前奥曼第曾率先带领费城管弦乐团访华演出,但在中美建交这个时代背景下,小泽老师和波交的访华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中方的宣传也更充分,令其影响更为深远,当年一些场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接连几次访华让小泽老师对中国的民乐作品和演奏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后来还特意邀请刘德海和姜建华等人访美,在Tanglewood音乐节上再度合作分别演出了吴祖强为刘德海改编的琵琶协奏曲《春江花月夜》,和为姜建华改编的二胡与管弦乐队版《江河水》。
小泽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时中央乐团从乐手技术到乐器质量和国外同行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小泽先生以极大的耐心辅导乐手进行排练。在第二次和中央乐团合作时发现乐手的乐器仍然很烂,实在看不下去,干脆主动安排送了乐团一批进口货。
小泽老师的老师卡拉扬就没有这么友好了。
79年10月,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首次访华,对接待单位和中方的合作乐手各种看不顺眼。不过这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卡拉扬的傲慢,这次访问一开始就出了个事故,当时柏林爱乐乘机到达北京时,机场的弦梯不够高,只好临时搭了几块木板接上。没想到柏林爱乐的三位乐手身手不够矫健,竟然从接缝里摔了下来,身负重伤,不得不马上被送回西德。这个事故让卡拉扬其后几天一直不爽,跟中方乐手合作时也没给好脸色。
不爽归不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和乐团主要成员还是按中方的安排参加了庆祝宴会。这次姜建华又被安排为外宾表演了《二泉映月》,出乎意料的是卡拉扬听后深受感动,一改之前对中国音乐家的态度,对姜建华赞不绝口。
更意外的是柏林爱乐的首席看中了小姜,当场邀请她去德国跟自己学小提琴,并且打包票说虽然小姜已经18岁了,从来没拉过小提琴,但是天份极高,改学小提琴一定能出类拔萃。
小姜开始以为人家是客气,没放在心上。可后来领导找她说德国人是认真的,一再跟中方催人呢。小姜思前想后觉得实在放不下二胡,只好借送机的机会当面谢绝了德国人的美意。
跟小泽老师本人力促波交访华不同,柏林爱乐的访华是当时西德政府在政府外交层面做出的文化交流安排。所以尽管卡拉扬本人有些牢骚,乐团方面仍然向中国元老指挥家黄贻钧发出了继续合作的邀请,不久以后黄老先生赴德指挥柏林爱乐演出了三场音乐会,曲目再次包括了刘德海领衔演奏的《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是中国指挥第一次指挥柏林爱乐,黄贻钧也成了第一位在柏林爱乐指挥中国作曲家作品的指挥家。
~土鳖扛铁牛~
小时候喜欢听热闹的,像部队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家陈耀星的《战马奔腾》听着就特别过瘾。经常听的还有像王昌元的古筝曲《战台风》,储望华改编的钢琴曲《翻身的日子》这样的作品。
成年后第一次出国到了新加坡,逛CD店见到一张香港马可波罗公司的二胡专辑《胡弓传奇》,演奏者陈军。除了《二泉映月》和《江河水》,还有《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和《战马奔腾》等熟悉的曲目。买回家一看介绍才发现这个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二胡艺术家”就是陈耀星的公子。
那差不多是世纪之交的时候,大众的文化生活形态有了很大变化,陈军那一批民乐演奏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要求新求变。
比如当时制作发行唱片在作品传播中已经占到了更大比重,追求发烧音效成了不可忽视的市场需求,录音师们各显神通,演奏家们也会更主动地尝试改良的乐器,适应新的录音技术。
另外为了吸引年轻一代的听众,也要求作曲和演奏者尝试新风格的编排和作品。也许是巧合,那个时期New Age风格在全球都有很高流行度。New Age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记忆当中有旅日的贾鹏芳推出的和平之月系列,张维良的天幻萧音,刘星的中阮,杜冲的排箫,稍晚还有林海蒋彦的琵琶语。哦,还有曹玉荣的流行音乐二胡改编曲,女子十二乐坊,台湾的风潮国乐。一时间好不热闹。
不过潮起潮落,似乎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风潮过后,很多听过就忘了,远不如青少年时代就耳熟能详的曲目那般记忆深刻。
一年多前在网上瞎翻,偶然间发现陈氏二胡世家的第三代已经出道了:
顺带的又发现不少电视竞秀节目《国乐大典》的视频,看上去十分火爆。陈家父女和方锦龙、唐俊乔等人十分活跃。
这又是民乐的一种新玩法了。
~土鳖扛铁牛~
你得到一枚通宝。谢铁手。
最近通货紧张,口头宝推。
琵琶相反而是《踏古》记得住,可能是因为现在低音和中间的打击乐吧?这也是现在许多国风的风格,比如之前说的《浮光》。《琵琶语》的古筝版也有印象。原版什么样早忘记了。
再说和平之月。贾鹏芳听起来太淡,恩田直幸太平直,只能留下个婉转的印象(邵容也是如此)。论淡,没有余味。论平,太过整齐。论直,只剩短促。依赖其他乐器的衬托,又不如伍芳。比起同人不一定好到哪去。相比之下,上海复兴计划就好得多。最后只留下了华音一张专辑,因为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乐器,适合催眠。
晚一点的,比如王俊雄、郑玮莹,不太容易描述,可以说是有点丰富,以至于显得有点吵闹,是上面平直的加强版。就像日本流行音乐那样同样的从头高到尾。看频谱尤其是Resonic的曲线波峰就很容易看得出来,一直有一个高度的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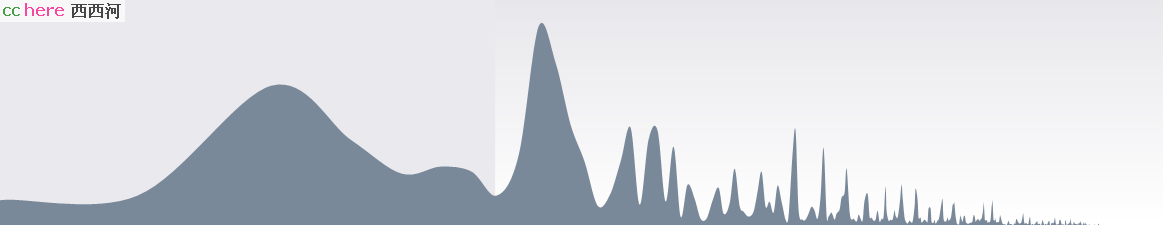
我觉得,除了第一印象之外,更主要的是没什么突破,只是突出了音色和大家印象里的风格。调高过于突出,听多了甚至耳朵疼。听Dubstep都不会这样的。
所以之前推荐了游戏音乐,比如逆水寒之点云集Ⅱ里的《瓷情一梦》、《不觉春深》等等,可以试着探索一下。虽然没玩过游戏,但至少比新世纪那些有特色。而且也提到另一种,也就是电子化,虽然受众有限。此外还有舞剧,比如张渠的白纻。像新赛马这类又快又响的反而不是喜欢的类型,很少接触。尽管提到过了此法玩琴的。但我觉得这类更接近表演艺术,而不是简单的听。
可能是我太过简单吧。
乐器的精致。由于木制暗色哑光为主,和钢琴、提琴还有金属小号的光鲜亮丽无法性比。大家也都有西方乐器的常识,而没有中国的,很难注意到那些细节。再有中国乐器的表演,往往是静默、淡然的,只有二胡、马头琴、大鼓之类激昂一些,难以像西方那样表现。文化传统也拒绝那种表演。就像琴诀里说的
尽管现在已经有很多了。
服装和气度类似,都可以做到,但问题在于风格。
表演场所是另一个关键。现在的场所是西式的,大家下意识想到的就不会是中国乐器。即便是全场关灯,聚焦在乐器表演者身上也是如此。和传统中国的差距很大。而建筑想要表现出中国风格,那可难于登天。不只是舞台、装修、灯光,连座位、布局都要考虑。再加上保持良好的视听条件,成本难以估计。
就算不用建筑,以舞台布置表现好了,用色彩还是形状?用灯光还是烟雾?哪些音乐合适?
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和曲子没进步无关,看看日本就知道,国内连煞有其是,连普及常识,维护文化地位都做不到,何来档次?这实际上是个文化思维问题,外表并不重要。看歌剧的时候,那些道具背景有时简直可笑,可是掉档次了吗?问题在于表演本身。
此外,我记得忙总说过一次就餐经历
进入四合院,中间一个小荷塘,满园的干冰雾气。进入大厅,满庭的明式官帽椅,初初觉得还有点味道,但是一眼看到大厅中央一个圆台上的美女大提琴手和竖琴手,再看到餐桌上的西式餐布和蝴蝶兰花盆,立即觉得真的不伦不类。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加上焚琴煮鹤,难以有大发展。本来高档并不是只在音乐厅才有,要大众化才行。看看大众作品里的音乐都是什么?八九十年代还算有发展,现在已经近乎停滞了。除了新兴媒体。
档次,实际上就是内涵和地位,外观并不重要。要知道人们总能发现巴黎的真相(巴黎综合征)。现在的问题是失语,长达一百年的裁剪、曲解和漠视,哪怕国家再怎么强调,渗透到骨子里的歧视不变,就不会有任何改观。因为那是决定一切发展的起点。
补:礼失求诸野。汉服开始是民间爱好者主导,我觉得音乐也有这个趋势。尤其是现在用音乐表达的成本越来越低了,缺失的审美也能自己补充了。地位随着中国发展也日趋回归。
中国近代,室内小舞台如乾隆皇帝的小戏台,室外大舞台是山陕会馆的戏台。
这些顶尖设计都不是为乐器演奏而准备的。
晋朝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到了清朝,还是共识。
新民族音乐是基于西方乐理的新创作,不是继承,是风格。
这个不是说,除了西方,别的地方就没可提的,印尼甘美兰的影响就比较大。
小时候听过的歌儿不少,大量的群众歌曲和民歌。其实很多时候是单位学校的大喇叭在放,作为日常活动的背景音乐接收的,久而久之很多曲调就刻在脑子里了:
《北京有个金太阳》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翻身农奴把歌唱》
《乌苏里船歌》和《新货郎》.....
改开以后这些歌曲就被认为不合时宜了,除了一些场合有群众自发传唱,正式的舞台和媒体上很少能听到见到。所幸当年一批音乐家选了不少改编成器乐演奏的版本,不至于让这些优秀作品从舞台上消失。
除了前面提到的《浏阳河》,还有《绣金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等。
这些器乐演奏的版本当然没有歌词,有些还把曲名中的时代色彩去掉,于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就变成了《向阳花》:
不过我本来对歌词就不太敏感,一首歌曲之所以为我喜爱,风格和旋律还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像我前面说过的,经过优秀作曲家的加工提炼,改编版本往往能给人带来更好的音乐体验。
我虽然生长在西安,对秦腔却完全无感,倒是十分喜欢陕北道情,碗碗腔,眉户(实际上是郿鄠,按方言念是"迷胡"),还有比较综合性的秧歌剧,比如《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里面有些歌词倒是印象很深刻,现在偶尔还能哼哼几句。大学期间正好同寝室里有一位同好,没事我们俩还经常对唱一段: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
放呀么放光明
什么字、放光明?
学习、学习二字我认滴清
这些风格的素材构成了很多更大型民乐作品的基础,回头还会聊到。
各地的民歌也听了不少,也是曲调熟悉,歌词印象模模糊糊。有意思的是一首《采茶舞曲》还是跟着侯跃文石富宽的相声学的😁:
80年代中期央视做了一期节目叫《跳动的旋律》,加了电声的民歌联唱,不到一个小时。我把节目录下来,之后几年里反复看了恨不得有上百遍,算是打了一针booster,连歌曲之间的很多过门儿都记得清清楚楚,不少歌词也忘不了了。
印象最深的是两位CP感十足的歌手王强和黄红英,他俩唱了《小放牛》:
赵州桥儿什么人修
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么咿呀嘿
赵州桥儿鲁班修
玉石栏杆圣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么咿呀嘿
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么咿呀嘿
还有那首《对花》:
正月里开滴是个什么花
那正月里开滴是蟠桃花
岂不知那花开有多么那个大
那七月里核桃是满园子青
奇不呀儿哟,花儿红
花不呀儿哟,楞噌噌
楞噌楞噌奇不楞登噌
那正月里花儿是开哩格红
歌手徐艺唱了《无锡景》:
第一个好景致呀要算鼋头渚
顶顶惬意夏天去避暑呀
山路喂曲折多优雅呀
水连着那个山来喂,山呀么山连水呀
还有《放风筝》
三月里来耶,是诶、清诶、明耶那一雅虎嘿
姐...姐...那个妹...妹去踏青呀啊
捎带着放诶风筝呀么那一呀呼嘿呼嘿
为徐艺伴舞的是海政歌舞团的小姐姐张雁,当时是惊为天人。
嘴有点歪的彝族妹子曲比阿乌唱了《拔根芦柴花》和《三杯美酒敬亲人》,姜志唱了《纺棉花》和《采茶灯》,张德富唱了《放马山歌》,胡少峰唱了《凤阳花鼓》:
左手锣,右手鼓
手拿着锣鼓来呀来唱歌
别滴歌儿我也不会唱
单会唱支凤阳歌
乒乒乓乓一个嗨呀
嘚儿郎当漂一漂,嘚儿郎当漂一漂,
嘚儿漂,嘚儿漂,嘚儿漂、嘚儿漂、嘚儿漂、嘚儿漂、漂漂一嘚儿、漂漂漂一漂......
当时还笑话他“嘚儿漂嘚儿漂”的卷舌音唱不出来。
对了,还有一个眉眼间含娇带俏的妹子霍艳梅,唱的《绣荷包》和《知道不知道》特别好听:
山青水秀太阳高
好呀么好风飘
小小船儿撑过来
它一路摇呀摇
为撩那心上人,我起呀么起大早
也不管那路迢迢,我情愿多辛劳
前几年冯裤子拍《天下无贼》时用了《知道不知道》,改得乱七八糟😠。
嗯,还有一位我们西安的冯健雪唱的《赶牲灵》和《兰花花》: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
蓝格嘤嘤地彩
一十三省的女儿啊
数上那个兰花花好
冯姐曾经去我们大学演唱,唱到一半现场扩音器坏了,冯姐耐心等师傅修好以后把前面几首歌重新唱了一遍,人品杠杠的。
几年前冯姐还随陕西歌舞剧院民乐团来芝加哥演出,眼见她上了岁数,腿脚似乎也不太好了,不禁有些唏嘘。
~土鳖扛铁牛~
这一篇采用广义的说法,对使用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演奏的作品不加区分。
当年有所谓的八大样板戏,很多人的印象里全都是革命现代京剧。实际上其中京剧只有五部,另有两部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还有一部交响音乐《沙家浜》。
这部交响音乐实际上还先于同名京剧被确立为样板戏之一,里面包括独唱重唱和合唱,配乐用了西洋乐队加上京剧的锣鼓家什,其实是类似于一部康塔塔。有意思的是歌唱演员都是唱美声的出身,短时间内突击学唱京剧居然也还像模像样。后来拍成了电影向全国推广,这也是我看到的版本。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些急就章,影响远不如京剧。
两部芭蕾舞的音乐创作更成熟一些,作曲家包括老一代的马可、瞿维和建国后留苏的中坚力量吴祖强、杜鸣心等一批大家。两部舞剧的音乐后来都被整理成组曲的形式,是现在音乐会上常见的曲目。
找不到合适的白毛女组曲视频,这是加了对唱的版本,注意乐队的声音大致看个意思:
很多年前李心草带中国交响乐团来本地访问,这是加演曲目之一。板胡的声音一出来我前面的一个伙计大呼一声“卧槽”😂。
根据舞剧音乐整理改编成组曲的还有《鱼美人》、《小刀会》等,也算上演比较多的。
我以前提过刚来美国时在图书馆找到一张杜鸣心老师的作品CD,这是其中的一首:
几部京剧里面,《智取威虎山》是于会泳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一部,老于在京剧伴奏里引进了西洋乐器,效果非常好。特别是打虎上山那段,圆号的乐声宽广深邃,既体现了林海雪原的空间感,又暗含着威虎山上的风云变幻,完美体现了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戏剧主题:
于会泳在后来的《杜鹃山》里对唱腔和韵白的改革更进一步,还尝试引进了主导动机的歌剧概念,回头看,那差不多就是现代京剧改革的顶点了。
我原来混过一个音乐论坛,有些网友是当年音乐戏剧创作改革的参与者,或他们的家人亲友,基本上所有人都一致认同于会泳的艺术天赋和他的贡献,唯一的争论是他到底应该算中国的格鲁克还是中国的瓦格纳😄。
于会泳后来的结局真是令人惋惜🙁。
还有一部《红灯记》,被改编成钢琴伴唱,倒是由几位剧中主演加上殷承宗完成了。
当然民族管弦乐绝对不仅限于舞台剧种的伴奏改编。
现在的音乐会上,《红旗颂》大概是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曲目
聆听此曲,抚今追昔,心潮澎湃,一股豪情油然而生。
《梁祝》应该是流传最广的华人音乐作品。它的前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位师生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后来大伙一商量,决定把它搞成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让提琴专业的何占豪和丁芷诺牵头主创。两人毕竟不是作曲专业,觉得搞不掂,又想拉本校作曲专业的陈刚加盟,陈刚说我忙着毕业作曲呢没时间啊。陈的导师丁善德是当时上音的领导,又恰好就是丁芷诺的父亲,于是小丁通过老爸做工作,硬把陈刚拉进了团队。
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顺便说一句,陈刚的父亲就是老一代的流行音乐歌王陈歌辛。
丁善德老师本人也是重要的民族管弦乐作曲家,代表作是《长征交响曲》等,他还是中国最早录制唱片的钢琴家,唱片曲目就包括贺绿汀的《牧童短笛》。
50年代去苏联学作曲的还有一位朱践耳,是相当高产的作曲家,创作了10部交响曲和一系列组曲和交响音诗。
还有一位陈培勋,代表作是交响乐《我的祖国》和交响诗《心潮逐浪高》。陈老还作有钢琴版的平湖秋月。
改开以后的音乐创作似乎经历了一些迷茫,倒是出了一批有天份的年轻人,大多出国了,而且这批人的作品跟前辈相比总觉得有些不接地气。
好在像鲍元恺、赵季平这样的前辈还一直有新作问世,年轻一代里像王丹红这样的也很值得关注。
鲍元恺原来也在我混的那个论坛实名发帖,还让网友对他当时的新作《炎黄风情》发表意见。
我们哪儿能发表什么意见啊,只能回帖说鲍老师加油!😂😜
~土鳖扛铁牛~
从历史上看,在演奏民族管弦乐中,(1) 完全使用民族乐器和 (2) 完全使用西洋乐器两种选择都有各自的不足。解决方案无非两种:一是在民族乐团里加入少量西洋乐器,来加强民乐团的短板,二是在交响乐团里加入若干民族乐器,来充分表现作品的民族特色。
这一篇里先用一个例子聊一聊第二种方式,把第一种方式的例子以及两类乐团的对比放在下一篇。
我想举的例子是由同名歌曲改编,在交响乐团加入竹笛、板胡、唢呐等中式乐器演奏的管弦乐《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我非常喜欢的是胡炳旭指挥中央乐团演奏的版本,可惜找不到类似版本的演出视频,只好用一个雨果唱片公司的录音来尝试一下。
管弦乐《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或者说原作歌曲本身使用了两首陕北民歌作基本素材,一个柔美抒情,另一个热烈奔放,用过去的话说,既能表现革命浪漫主义,又能表现革命英雄主义。
乐曲一开头先是几声竖琴,然后由中式竹笛吹奏出一段引子,此刻我想不出有哪件西洋乐器的声音能比这种灵动的竹笛音色更好地呈现如此鲜明的民族特色。倒是听过使用长笛代替的版本,效果差远了。
经过乐团加入后的一段连接,双簧管奏出了柔美的山丹丹主题,简直美哭了。上面那句关于竹笛的话现在恐怕要反过来说了,至少在当年我还无法想象这种稳定的气息和内敛的音色能用哪种民族乐器代替(这两年有一些变化,下篇细谈)。
接下来管弦乐各个声部先后加入,重复两遍这个主题。
然后画风一变,音乐开始热烈奔放的第二段,同样的主题将多次反复。
在引导部分的乐团齐奏中出现了唢呐和板胡两个富有个性的声音,但此时还比较克制,而且几小节后就安静下来,把时间交给管弦乐声部完成这一段主题的第一次呈现。
当此段主题第二次出现时,傲娇的板胡大着嗓门担当了主角,弦乐用拨弦加以衬托,下方似乎还有几声琵琶隐约相伴。此刻在原来的歌词中正是热腾腾的油糕米酒端上来的时候,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第三次反复时,由增强力度的弦乐声部开始,唢呐板胡等再次加入后逐渐把情绪往上带。
第四次是原歌唱到“满天的乌云哎呀哎嗨哟,风吹散,咳哎咳哟”的时候,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减速用厚重的织体表现这一意境,然后“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音乐在豁然开朗的气氛中来到第一个高潮,乐队上方撒着欢的唢呐简直是神来之笔!
接下来没有任何停顿,各交响声部以饱满的热情重现首段音乐里的山丹丹主题,然后用温暖舒缓的圆号声略微平复一下听者的情绪。
此时久违的竹笛声再次响起重复这个主题,竖琴在一旁轻柔地陪伴。和它第一次出现时相比,竹笛的乐声又多了几分百转千回,这个情绪由整个乐队进一步发展,再次把音乐推向高潮,在顶点处由几声坚实的定音鼓完成了最终的情感宣泄。
最后,全曲在轻柔的竖琴和弦乐拨弦中和缓地结束。
回看整个乐曲,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各有擅场又水乳交融,配合得天衣无缝,堪称同类曲目中的优秀之作。
~土鳖扛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