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量子》重启贴 -- 奔波儿
- 共: 💬 83 🌺 1075
用微信聊天的时候,朋友提起了自己以前翻译的《量子》。这才想起,这个大坑,自己已经扔了快五年了,成了柳京塔那样的烂尾工程,简直是一座耻辱柱。
这些年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在事业和家庭中忙忙碌碌,好像逐渐迷失了自我。偶尔,在夜深人静之时,又想起了自己在“丁”字楼的读书生涯,虽已是多年前的往事,那些欢乐和悲伤,依旧历历在目。
前阵子,帮助朋友翻译的书稿顺利出版。那些和自己的专业完全不搭界的玩意儿,自己都能翻得兴趣盎然,那和自己专业相近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尽个心呢?更何况,这是自己在酒后对一位挚友许下的一份承诺。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数年,而大家已经是相隔万里之遥,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既然如此,何不重启《量子》的翻译?先校译以前翻译的段落,然后一气完成所有内容。
以此贴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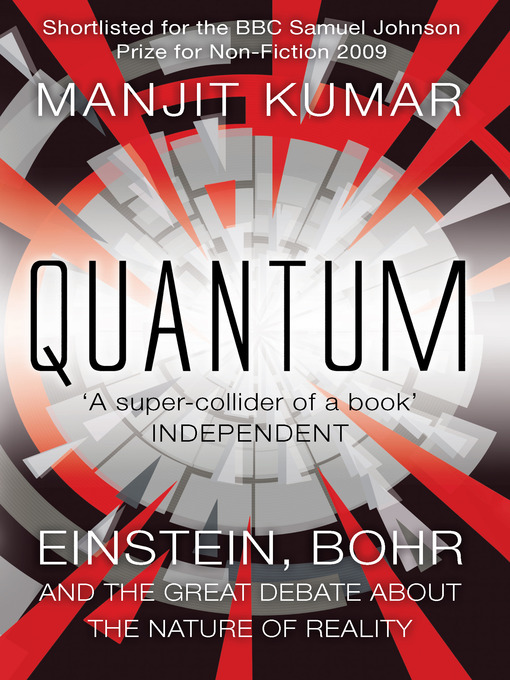
---------------------------------------- 爬呀,爬呀,爬楼梯呀 --------------------------------
很喜欢读科普类书籍,先谢了!。
最喜欢《时间空间和万物》
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泪水盈眶,他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再过几天,他即将参加一次会期长达一周的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量子物理学家们将会认真探讨一下他们所创造的这一革命性的理论体系。他会告诉自己的老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他已经决定站在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一边。埃伦费斯特,奥地利人,时年34岁,是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理论物理学教授,他赞成波尔的理论,认为原子的世界是奇妙而精致的。
有一次,在会议桌边,埃伦费斯特给爱因斯坦写了张小纸条---“别笑!每天,咱们都得被迫听上经典物理学家们在那儿唠叨上十个小时,对于量子物理学家们而言,这不啻于就是一场炼狱。”“我发笑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幼稚了。”爱因斯坦回复道:“让我们等瞧着吧,再过上几年,看看到底谁能够笑在最后?”在爱因斯坦看来,这并非什么笑料,而是事关物质世界的本质以及物理学的灵魂。
1927年10月24至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五届索尔维会议(Solvay Conference),讨论的主题是“电子与光子(Electrons and Photons)”。在下面这张合影上,汇聚了那些在物理学史上最激情澎湃的人和事。在与会的29人之中,有17人先后赢得了诺贝尔奖(Nobel Prize),可以说这次会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聚会之一。它标志着物理学黄金时代的终结,自打伽利略和牛顿在17世纪发起的那场科学革命以来,这一科学创新的时代,无与伦比。
保罗·埃伦费斯特站在最后一排左数第三位,身体微微侧倾。前排就坐的一共九人,包括一位女士和八位先生,其中有六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或化学奖金。而那位女士,一人就获得了两项,包括1903年的物理学奖和1911年的化学奖,她的名字是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居中正坐的那位也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是自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目视前方,右手抓着椅子沿儿,看上去有些紧张。难道是浆洗过的衬衣领子和系在脖子上的领带让他不舒服?或者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他听到了什么?坐在第二排最右侧的那位先生是尼尔斯·玻尔,他看上去很惬意,脸上浮现的笑容却有点儿古怪。在这次会议上,他收获颇丰,但是,在他即将返回丹麦的时候,他还是有些郁郁寡欢,因为他没能说服爱因斯坦接受他的“哥本哈根诠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理论。
爱因斯坦并没有俯首称臣,而是花了一周时间试图解释量子力学(与试验观测)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说波尔的“哥本哈根诠释”理论是有问题的。几年以后,爱因斯坦评述道:“这一理论在我看来就是一位智商超群的妄想症患者的幻觉,其中充斥着各种语无伦次的思想元素。”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坐在居里夫人的右侧,手上拿着帽子和雪茄,正是他发现了量子(Quantum)。1900年,普朗克被迫接受了光能以及其它形式的电磁辐射在被释放或者吸收的时候,是以单位能量的整数倍形式存在的。“Quantum(量子)”是普朗克用来命名基本单位能量的一个名词,其复数拼写就是“Quanta”。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能量的释放和吸收是一个连续过程,就像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一样,而量子能量的提出则是与这一传统观念的撤离决裂。在牛顿力学所统治的宏观世界中,水是可以从水龙头里面滴出来的,然而能量却不能够像大小不一的水滴一样进行传递。但是,在原子和亚原子的世界,却是量子的势力范围。
当时,物理学家们发现原子内部的电子所拥有的能量是量子化的,且仅为单位能量的整数倍。在人们所熟悉的宏观世界中,能量以及其它物理特性的变化则是平稳和连续的,例如从A点移动到C点,必须要经过(两点之间的)B点;至于微观世界,它并非宏观世界的微缩版,在这个尺度上,许多物理特性都具有和能量一样的特性,即其变化是非连续的,甚至可以说有些匪夷所思。量子物理研究发现在原子内部,电子可以在某一时刻处在某个位置,通过释放或者吸收一份能量,它就能瞬时出现在另外一个位置,而不需要经过这两点的中间地带中任何一点,整个过程就像变魔术一样。这种现象用经典物理学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人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物体刚才还在伦敦,可一瞬间就出现在巴黎、纽约或者莫斯科呢?
在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量子物理学发展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可以说还处于非常零散和初级的阶段,更甭提什么严格的逻辑结构。在这种危机四伏乱象纷呈的时候,物理学家们勇敢地推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直到目前为止,在很多学校的课堂上,老师们讲解的原子模型还依旧像一个小小的太阳系,原子核居中,电子沿着自己的轨道绕其运行。这种模型早就被量子物理学家们扔进了垃圾堆,在他们看来,人们根本就无法观察到原子的存在。1927年,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就发现了这一与一般常识相左的现象,这位德国量子力学神童(Wunderkind)敏锐地抓住其问题实质,并提出了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又称“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根据他的理论,如果你想准确测定一个粒子的速度,则你不可能同时测定其精确的位置;反之亦然。
当时,无人能够解释量子力学的方程,也无法说明该理论是如何在量子的尺度解释物质的本质。从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时代开始,哲学家们就一直在讨论因果问题(Cause and Effect),以及如果人们没有看到月亮,那月亮是否还存在这类问题。而在量子力学被提出以后,这帮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了。
在索尔维会议召开的时候,量子物理的基本组成要素已然成形,与会的诸位物理学家们共同书写了我们这部关于量子的故事的第一乐章。而在爱因斯坦和波尔之间的争论所激起的思想火花,给了无数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以灵感,其影响绵延至今,例如:物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描述一件事实才真正有意义?“这一争论的影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P. Snow)认为:“很遗憾,我们根本无法用现有的货币单位去衡量其价值。”
在这两位主角中,爱因斯坦被视为20世纪的偶像。有一次,他受邀在“伦敦守护神(London Palladium)”剧院做了为期三周的报告。当他出场的时候,许多妇女居然兴奋过度而晕倒在地。而在日内瓦,他被年轻姑娘们疯狂追捧。现而今,这种景象只会出现在流行歌星或者电影明星们身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19年,当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会出现弯曲的现象被证实以后,他成为了一位科学界的超级明星。1931年1月,爱因斯坦在美国各地进行学术演讲,在这期间,他出席了查理·卓别林(Charlie 1889~1977)所拍摄的《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首映式,被人狂热追捧的一幕再次出现。“人们对我欢呼是因为他们都看懂了我的电影,”卓别林对爱因斯坦说:“但他们向你欢呼却是因为根本就没人懂你的东西。”

当“爱因斯坦”这个名字成为天才科学家的代名词的时候,尼尔斯·玻尔却名气有限,直至今日仍未能得享盛名。但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人而言,他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巨人。德国犹太裔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23年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玻尔对于理论和实验物理学的深远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物理学家”。四十年之后的1963年,维尔纳·海森堡依旧认为“玻尔对于物理学以及我们这个世纪所有物理学家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个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20年,爱因斯坦和玻尔在柏林第一次见面,他们发现彼此是一对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好伙伴,而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战斗”不但没有带来丝毫的苦涩和仇怨,反而推动彼此不断修正发展各自对量子问题的思考。也正是通过他们俩以及其他那些会聚在索尔维会议上的物理学家,我们今天才能回顾那个激动人心的量子时代。“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还只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后来回忆“当时,物理学家们长时间泡在实验室里,他们做了很多重要的实验,并不断取得大胆的突破,但他们往往在开始阶段漏洞百出,而且所得到的结论也时常似是而非。在相互间的探讨中和学术会议上,他们彼此争辩着,批判着,并不时用精妙绝伦的公式来一段数学的即兴演奏。对那些参与其间的人们来说,那是一个充满着创造力的年代。”但同时,正如奥本海默这位原子弹之父所言“他们一次次新的发现带给他们的,不但有骄傲,还有恐惧。”
离开了量子,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将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根据量子力学的理论,人们无法通过实验观测来确定一个事物是否存在,这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已经被物理学家所接受。美国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默里·盖尔曼(Murry Gall-Man:1929~今天)将量子力学描绘为“那是一个神奇的让人迷乱的世界,尽管我们谁都不能真正了解它,但却知道如何利用它。”的确,我们早已经在利用它了。量子力学推动和筑就了我们这个现代世界,它的影响深入到了诸多领域,包括从计算机到洗衣机,从移动电话到核武器。
量子的故事要从19世纪末开始说起。当时,人们已经做出了许多重大发现,比如电子、X射线、放射性,关于原子是否存在也是当时的热点议题之一,许多物理学家自信地认为所有重要的物理发现都已经完成。“比较重要的基本法则和物理现象已经全部被发现,并且被不断准确证实,因此这些知识被取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麦克逊(Albert Michelson:1852~1931)在1899年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另外,他还断言:“我们未来的发现不过是在小数点六位以后再加上点什么而已。 ”当时,很多物理学家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相信任何尚未解决的物理问题不过是对已有的物理学知识做点缝缝补补的工作,而且早晚会臣服在那些经历过岁月洗礼的理论和定理的脚下。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这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早在1871年就对这些自大狂们告诫道:“现代实验是通过不断地测量进行的,这一特点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在数年之间,所有那些伟大的物理常数都将被更加准确地计算出来,而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通过实验在小数点后在添加上数字”但是,麦克斯韦指出对于那些认认真真做观测的人们来说,真正的奖赏并不是取得更高的准确性,而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发展新的科学思想”。而量子力学正是这一“认认真真的观测”所取得的成果。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的一些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们正痴迷地研究一个困扰了他们很久的问题:对于一根滚烫的拨火棍,其色光范围、光强与温度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和当时物理学家所热衷的X射线和放射性问题相比,简直就是鸡零狗碎的东西。但对于一个刚刚在1871年建立的新国家来说,如果德国物理学家们能解决这个与一根烧得滚烫的拨火棍相关的问题,即著名的“黑体问题”(Blackbody Problem),也就意味着帮助德国照明工业在与美国和英国同行的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但是,尽管这些德国最棒的物理学家竭尽全力,但却屡战屡败。1896年的时候,他们曾经认为他们成功了,但随后几年中新的观测数据表明他们依旧失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马克斯·普朗克,他付出的代价就是量子。
不说话而已
“简而言之,我干的就是一件铤而走险的事情。”
---马克斯·普朗克
“就好比我们把地层翻了个底朝天,地基都不牢靠,而我们却要在上面盖房子。”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有些人初次接触到量子理论,但却无动于衷,很有可能他们根本就不理解这些东西。”
---尼尔斯·玻尔
马克斯·普朗克在回顾他漫长的一生时,曾经这么写道“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说服反对者来取得胜利的,而是因为那些反对者都逐渐故去,而新的一代人慢慢熟悉了这种新的理论,并渐渐成长起来。”按照一般的俗套,普朗克应该“铤而走险”为自己写一份科学讣告,宣布放弃他长期以来所珍视的那些物理理论。普朗克外套深色西装,内着浆洗过的雪白衬衣,打着黑领结,看上去就像一位标准的普鲁士公务员,但是“在他硕大的额头下,有一对洞悉一切的眼睛”。他做事属于典型的老派风格,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做其他事情,他都小心谨慎。“我的格言就是”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提前仔细考虑好每一个步骤,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能为自己的决断负责,那就冲吧,什么都甭想拦住你。”普朗克并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普朗克在学生面前总是保持着一成不变的态度和仪容,正如有人后来回忆,“真让人不可思议,迎来这场革命的人居然是这个人。”的确,就是这位欲拒还迎的革命者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一事实。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喜欢“平稳地过渡”,而避免“未知的冒险”。他坦承自己缺乏“对于智慧火花的快速应变”,为此他经常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将新的理论与自己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调和在一起。在他42岁的时候,普朗克于1900年的12月提出了解释黑体辐射分布规律的数学公式,这一发现无意间点燃了量子革命。
任何物体,只要足够热,就能辐射出热量和光,其强度和颜色会随着温度发生变化。如果将拨火棍的一端放在火上烤,首先会变成暗红色,随着温度升高,会变成樱桃红,接着是亮黄橙色,最后变成蓝白色。如果将拨火棍从火上拿开,棍子会逐渐冷却,其颜色会反向变化直至不再发出任何可见光。然而这时候,棍子依旧能够释放出肉眼无法分辨的热辐射。如果让棍子继续冷却,过上一段时间,连这种不可见的辐射也将消失,人们这时就可以触摸拨火棍了。

1666年,时年23岁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发现,如果让一束白光通过三棱镜,白光会分解成一条七色光带:红,橙,黄,绿,蓝,靛,紫。红色和紫色是否界定了光谱或者人类所肉眼所能观察到的光线?这个问题在1800年有了答案。那一年,已经有了异常灵敏和精确的水银温度计,德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1738~1822)将这样一个温度计放在一束七色光谱前面,他发现当他缓慢移动温度计从紫光开始一直到红光,温度是一路上升的。让他吃惊的是,当他将温度计移到红光外侧一英寸时,温度继续上升。他的这一发现后来被命名为“红外辐射”(Ultrared Radiation),这种光辐射对于肉眼是不可视的。1801年,德国化学家约翰·里特(Johanna Ritter:1776~1810)利用硝酸银接触光线会变暗的特点,发现在七色光谱的另一端,即紫光外侧也存在着不可见光---“紫外辐射”(Ultraviolet Radiation)。
很久以来,陶瓷工人们就熟知,每当物件被加热到特定的温度时,就会发出特定颜色的光。1859年,德国物理学家古斯塔夫·基尔霍夫(Gustov Kirchhoff:1824~1887)时年34岁,他在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任教期间,开始着手研究这一现象。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基尔霍夫构思了一个能够完全吸收和释放辐射的理想状态的物体,也就是“黑体”的概念。他这个构思非常巧妙,因为一个能够完全吸收辐射的物体,不会反射出任何光线,所以看上去是黑色的。但是,任何一个完全释放辐射的物体只要被加热到能够释放出可见光时,其颜色可以是除了黑色以外的任意一种颜色。

基尔霍夫所假想的黑体是一个简单的中空物体,在其外壁上存在一个小孔,可见光或不可见光辐射可以通过小孔进入黑体内部,实质上小孔就是这个所谓“黑体”的关键所在。在黑体内腔,光线在内壁上被反复反射,直至完全被吸收。另外,该黑体的外壁应该是绝热的,当其被加热时,内壁释放出辐射,并充满黑体整个内部空间。
开始的时候,内壁就像一个烧红的拨火棍一样,呈现为樱桃红色,但实质上呢?这个时候,真正释放的能量主要是红外辐射。接着,当温度继续上升时,内壁变为蓝白色,辐射波长将覆盖红外线到紫外线整个光谱范围。这时,小孔就成为一个完美的辐射释放体,因为,通过该小孔可以采样到当前温度下黑体内部所释放的所有波长的辐射。
基尔霍夫在数学上分析了陶瓷工人们在陶瓷窑中观测到的辐射现象。根据基尔霍夫定理的描述,黑体内腔的辐射频段和强度与黑体的构成材料无关,也与其形状和尺寸等其它因素无关,而仅仅取决于温度。就这样,基尔霍夫非常巧妙地将拨火棍问题简而化之---在某一特定温度下,黑体所释放的辐射光谱的频段与其强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在该温度,黑体所辐射的能量为多少?这就是著名的“黑体问题(Blackbody Problem)”。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基尔霍夫及其同事需要完成大量的工作,包括测定黑体辐射从红外线到紫外线各个波长上的能量大小和频率范围,以及推导出温度与能量之间的关系式。
这一假想的黑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尽管基尔霍夫无法通过做实验来推进自己的研究,但他却给物理学家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假想中的黑体的物理特性与其构成材料无关,也就意味着用以描述其特性的数学公式只应该包含两个变量,即:黑体的温度和其所释放的辐射的波长。因为过去大家认为光是一种波,所以想区分出不同的颜色和色调,只需要知道其波长,也就是相邻波峰或者波谷之间的距离。波的频率被定义为一秒之内,经过任一个固定点的波峰或者波谷的数目,因此频率是与波长成反比的。波长越长,则频率越低,反之亦然。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等效方法可以测定波的频率,也就是一秒之内,波上下起伏(波动)的次数。

要想构建一个真实的黑体,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另外,当时也没有能够足够精密测定辐射能量的仪器,导致物理学家们在其后四十年之内举步维艰。这种停滞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德国公司想研制一种更加高效的电灯泡,以击败他们的英美竞争者。而想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测定黑体的光谱,并找到基尔霍夫设想中的方程式。
在电器工业迅猛发展的年代,人们创造了一系列新发明,包括电灯、发电机、电动马达、电报等,而这一长长的列表上最后一个就是白炽灯。随着这些新发明不断涌现,人们普遍而迫切地感到有必要设定一套电学单位和标准。
1881年,来自22个国家的250位代表汇聚在巴黎,参加第一届国际电学单位制定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Electrical Units)。包括伏特、安倍等单位先后被与会者定义和命名出来。但是,在亮度这一重要指标上,大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对节能照明设备的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在任一温度下,黑体均为最佳的光能释放体,它(在理论上)能够通过消耗最少的热能来释放出最大的亮度,因此是用以标定和制造电灯泡的最佳参照。
作为工业家和电动机的发明人,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写道:“在这场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中,最先下手并能最先投入生产的国家就能一掌乾坤。”为了独占鳌头,德国政府在1887年建立了Physikalisch-Technische Reichsanstalt(PTR),也就是“皇家物理技术研究所”。西门子在柏林郊区的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捐出一块土地,建在这儿的PTR被视为德意志帝国与英国和美国一较高下的法宝。经过十年以上的修建,PTR全部建筑群才完工,而PTR也成为世界上装备最为优良也是最昂贵的研究所。它的使命就是通过发展各种标准和测试新产品,帮助德国站在科学应用的最前沿。制定一个能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的亮度标准成为PTR优先考虑的使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PTR开展黑体研究的驱动力就是发明一只更好的照明灯泡。这一研究导致了一个人在无意间发现了量子,这个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出现的正确的人就是普朗克。
![]()
![]()
![]()
普朗克的全名为马克斯·卡尔·恩斯特·路德维希·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他于1858年4月23日出生在基尔(Kiel)市,他的家族是为教堂和政府工作的,而基尔所在的荷尔斯泰因(Holstein)州当时还是丹麦的一部分。普朗克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著名的神学家,而他的父亲是慕尼黑大学的宪法学教授。这些热爱上帝和世人法则的男人们恪尽职守,性格坚毅,忠于祖国,马克斯也是这样一个人。
普朗克所就读的马克西米利安中学(Maximilian Gymnasium)是慕尼黑市最著名的中学。普朗克在班上总是位居前列,虽说从没有得过第一名,但他通过刻苦学习和严格自律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当时德国的课程设置就是鼓励学生通过死记硬背学习实用知识,而普朗克就是这一体制的优良产品。在一份学校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尽管有些孩子气......十岁的普朗克思维清晰、逻辑缜密.......他将成为一个出色的人。”在他十六岁的时候,普朗克对酒吧敬而远之,而非常喜欢去剧院和音乐厅。作为一个天才的钢琴家,他甚至产生了努力成为一位职业音乐家的想法。因为对此心存疑虑,他向人征询意见,结果别人一点不留情面,告诉他说:“如果你真的要问,建议你最好去学点别的什么”。
1874年10月,16岁的普朗克进入了慕尼黑大学,并选择学习物理学,因为他强烈地想探寻自然的奥秘。与准军事化管理的中学相比,德国大学则给予学生们几乎完全的自由。没有人督促你的学业,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学生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可以任意选课。那些喜欢学术的学生就这样一步步走入最好的大学,投入到最杰出的教授门下学习。普朗克在慕尼黑待了三年,有人对他说“物体学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进入的领域,那儿已经没什么值得发现的东西了”,于是他决定转学,进入了德语区最顶尖的大学----柏林大学。
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被锻造出来,而柏林就是这位欧洲新贵的首都。柏林位于哈维尔河(Havel)和施普雷河(Spree)之间,法国的战争赔款被大笔用在柏林的市政建设上,这将是一个能与伦敦和巴黎比肩的城市。1871年的时候,柏林的人口是86.5万,而到了1900年,人口暴增到接近200万,而柏林也成为了欧洲第三大城市。当时,在东欧地区掀起了一场排犹风潮,特别是在沙皇俄国,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杀,很多人被迫逃难来到了柏林,成为这座城市的新移民中的一群。人口的激增导致房价高企、物价飞涨,许多人无家可归穷苦潦倒。城市的一些街区成了平民窟,连纸板商都在打出的广告上吹嘘自家的纸箱子“价廉物美,适宜居住”。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还是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融入到柏林这座城市,而德国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工业蓬勃发展,经济高速增长。德国统一以后,原来因为封建割据所带来的苛捐杂税随之消失,同时,法国缴来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德国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德国生产了整个欧洲大陆2/3的钢铁,一半的煤炭,而其发电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总和。1873年,由于股票市场崩盘导致整个欧洲进入经济衰退和恐慌期,但这一切仅仅让德国飞速发展的步伐略微减慢了几年。
德国统一激发出德意志帝国的雄心壮志,德国人想让柏林大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德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 von Helmholtz:1821~1894)被从海德堡聘请来。亥姆霍兹同时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他发明了验眼镜,帮助人们了解人眼的工作原理。这位年过半百知识渊博的智者知道自己的价值,他的薪酬是普通水平的好几倍,另外,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建一所全新的研究所。该研究所是1877年开建的,那一年,普朗克转学来到了柏林大学,开始去主楼里上各种课程。该建筑坐落于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以前是一处王宫,正对着柏林国立歌剧院(Opera House)。
作为一名教师,亥姆霍兹并不称职。“这一点显而易见,”普朗克后来说:“亥姆霍兹从来不好好备课。”古斯塔夫·基尔霍夫也是从海德堡过来的,他备课倒是非常认真,但是讲的课呢,“就像是一本行文准确的课文,干巴巴的,单调乏味”。对满怀希望寻求科学火花的普朗克来说,“这些人讲的课让我觉得自己是竹篮打水。”为了抚慰自己“渴求先进科学知识的心灵”,普朗克偶然读到了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1822~1888)的著作,克劳修斯当时是波恩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和普朗克所遇到的那两位讲课平淡无趣的著名教授相比,克劳修斯拥有“清晰而充满启发的逻辑思辨”,这让普朗克为之着迷。当他读到克劳修斯所写的热力学论文时,那种久违的对于物理学的热情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当时,热力学被用来解释热量,以及它与其他各种能量形式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理论主要包含在两大定理中。第一定理是用一个严谨的公式,它指出能量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总是保持守恒。能量既不会自己生成,也不会消失,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树上的苹果在树上挂着的时候就具有了一定的重力势能,当它落下来的时候,苹果的势能就转化为动能。
普朗克在第一次接触能量守恒定理的时候,还是一个中学生。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定理给自己的感觉就像“一道神启”,因为它反映了“大自然绝对的永恒的规律,不受任何人类的干扰”。就是在那一刻,他窥视到了永恒的奥秘,从此他把追寻大自然这些绝对的基本的法则视为“生命中最高尚的科学追求”。这时,普朗克正沉浸在克劳修斯所推导的第二热力学定理——“热量不会自发地从冷处转移到热处”。冰箱的发明正是克劳修斯所说的“自发”过程的最好例证。通过从外部获得能量,比如说电能,冰箱使热量能够从低温处转移到高温处。
普朗克认为克劳修斯的定理并非像表面上看去那么简单,而是具有伟大的意义。由于温差的存在,能量从A点转移到B点,这与大家日常所观察到的很多现象都是吻合的,比如一杯热咖啡会逐渐变凉,而一卷冰激凌会慢慢融化。如果没有人为干预,反向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为什么不会呢?能量守恒定律并没有严禁一杯热咖啡变得更热而同时其周边的空气变凉,或者一杯水变热而(同一杯子中的)一块冰变得更凉。它并没有剥夺能量自然地从冷处传递到热处的权利。然而却有什么东西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克劳修斯将其命名为“熵(Entropy)”,它解释了在自然界中为什么某些过程会发生,而另外一种过程却不能。

当一杯咖啡变凉的时候,咖啡周边的空气会逐渐变热,咖啡的热能逐渐散失,并一去不复返,而相反的过程却不会(自然地)发生。假定能量的守恒就是大自然用于掌控各种物理交易的法则,大自然当然有资格为每一笔交易制定一个价格。正如克劳修斯指出的,“熵”就是这个交易能否进行的价格。在任何封闭的系统中发生的物理过程,熵只能保持不变或者增加,而任何引起熵减少的过程则是严格禁止的。
克劳修斯所定义的“熵”也就是某一物体或者系统中流入或者流失的热量除以其温度。假如一个温度为500度的热物体传递了1000份能量到一个250度的冷物体,则该热物体的熵值的变化量为-1000/500=-2。原来温度为250度的冷物体则因为获得了1000份能量,所以其熵值增加量为1000/250=4。对于这两个物体所组成的总的系统而言,其熵值增加量为2。因为所有真实发生的过程都会导致熵的增加,因而是不可逆的。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阻止了热量自然地从冷处传递到热处。在理想状态下,只有当熵值不变时,一个物理过程才是可逆的。可是,这样的过程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物理学家的思想中。至于宇宙,它的熵值将不断变大。
除了能量,普朗克认为熵是“物理系统中最重要的特性”。在柏林大学待了一年之后,普朗克又回到慕尼黑大学,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普朗克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他进入物理学术殿堂的一块敲门砖。可令他感到绝望的是,“包括那些与他的研究问题有关联的物理学家在内,几乎没人对他的研究感兴趣,更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亥姆霍兹根本就没有读他的论文;基尔霍夫倒是读了,但却不同意他的观点;至于那位对他影响如此深远的克劳修斯,对他的问题置之不理。普朗克在70年之后甚至还略带苦涩地回忆说“当时,这些物理学家对我的论文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在他自己“内心的驱动”之下,普朗克一往无前。热力学,特别是第二定律,成为了普朗克研究的关注点,也就是从这一步起,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科学生涯。
德国大学都是国立学府,所有的辅助教授(助教)和普通教授(正教授)都是教育部聘用的国家公务员。1880年,普朗克成为慕尼黑大学的一位不拿薪水的讲师(Privatdozent)。无论是国家还是大学都不会付他一分钱,听他课的学生所交的学费就是他的收入。五年时光,他徒劳地等待着一个辅助教授的位置。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对做实验不感兴趣,获得晋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理论物理学在当时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研究领域。一直到1900年,整个德国只有十六位理论物理学教授。
如果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普朗克明白自己“必须在科学领域扬名立万”。哥廷根大学宣布将开展一次论文竞赛,竞赛题目是“能量的本质”,普朗克的机会终于来了。1885年5月,普朗克正忙着写论文,这时,传来“一个让人彻底解脱的好消息”,基尔大学给了27岁的普朗克一个辅助教授的职位。他怀疑自己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位,是由于自己的父亲与基尔大学物理系的主管有交情,因为他知道还有很多更有名的求职者比自己更有可能获得这份工作。普朗克接受了这个职位,在他回到家乡不久,就向哥廷根大学的竞赛组织方递交了自己的论文。
在哥廷根大学举办的这次学术论文大赛中,仅有三篇论文参加,最终结果的发布却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而且没有获胜者。普朗克的文章倒是获得了第二名,但是因为他在一次学术辩论中站在亥姆霍兹这一边,得罪了与其唱反调的一位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因此本该获得的奖金也化为乌有。这帮学术判官们对普朗克的不公平对待反而引起了亥姆霍兹对普朗克及其研究工作的注意。1888年11月,在基尔大学待了三年多以后,普朗克收获了一份意想不到的荣誉。基尔霍夫去世以后,柏林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职位有了空缺,求职者纷至沓来,普朗克也投了简历,可他在诸多候选人之中既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但是在其他候选人纷纷被刷掉以后,凭借亥姆霍兹的支持,普朗克成功地获得了理论物理学教授一职。
1889年的春天到了,这时的柏林不再是普朗克十一年前离开时候的模样,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取代了露天排水沟,以往那些让游客退避三舍的刺鼻恶臭“风光”不再,一到晚上,星星盏盏的街灯就照亮了所有的主街。亥姆霍兹这时已经不是柏林大学物理系主任了,而去执掌距离柏林大学三英里以外的德国物理技术研究所(PTR)。他的继任者是奥古斯特·孔德特(August Kundt:1839~1894)。孔德特虽然没有参与聘用普朗克这件事,但他还是热情欢迎普朗克的到来,称其为“一位优秀的教员”和“一个能干的人”。
1894年,73岁的亥姆霍兹和55岁的孔德特在数月间相继离世。普朗克在进入柏林大学两年以后被晋升为正教授,成为这座顶尖大学的高级物理学家,时年36岁。面对越来越重的责任,他别无选择,其中一项新的工作就是为理论物理期刊《物理通报》(Annalen der Physik)做顾问。这个顾问的位置非常重要,因为他对提交给这个最为权威的物理学期刊的所有论文有一锤定音的权利。位置越高,压力越大,同时也因为自己的两位同事的病逝,普朗克心怀忧伤,他只有把所有的愁苦转化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作为柏林物理学界中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在PTR所开展的、并受到工业界大力推动的黑体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时,就关注着这项研究。要想研究黑体辐射的光和热,热动力学是关键,但由于缺乏可靠的实验数据,普朗克无法推导出基尔霍夫所揣测的那个虚构的公式。很快,他的一位在PTR工作的老朋友取得了一项突破,普朗克不得不直面黑体问题。
1893年2月,29岁的威廉·维恩(Wilhelm Wien:1864~1928)发现一个简明的数学公式(即维恩位移定律),可以用来描述黑体辐射与温度变化的关系。维恩发现黑体的温度越高,其释放的峰值辐射的波长就越短。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温度的升高会导致辐射总能量的增加这一现象,但维恩的“位移定律”却给出了更加精确的描述:峰值辐射的波长与黑体温度的乘积是一个常数。当温度加倍时,波长的“峰值”只有以前长度的一半。

维恩的发现说明如果通过测量波长的峰值(即某一温度下最强辐射的波长)算出该常数,就可以反过来通过测量温度得到峰值波长。另一方面,维恩的公式也可以用来解释拨火棍烧红以后其颜色随温度变化的现象。当温度较低时,拨火棍释放的是主要是自红外线开始的长波长辐射。随着温度的升高,其释放的辐射的峰值波长会变短,也就是说会逐渐向短波长“移动”。与此相应,拨火棍的颜色从红色慢慢变成橙色,然后变为黄色,随着光谱中紫外线一侧的辐射增强,最后变成了蓝白色。
维恩既是一名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实验员,他迅速地使自己成为物理学家这一濒危物种中的一员。需要说明的是,维恩是利用业余时间发现的这一位移定律,而且是在未得到PTR的出版许可前就以私人通信的名义发表了论文。当时,维恩在PTR的光学实验室工作,是奥托·努玛(Otto Lummer:1860~1925)手底下的一名助理实验员,他日常工作就是为黑体研究做一些实验。
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造一架性能更好的光谱仪,这个仪器将被用来对比不同光源(例如:煤气灯,电灯)所释放的光强度,即在一定波长范围内所释放能量的多少。1895年的秋天,努玛和维恩发现了一种新的改进型的中空黑体,可以将其加热到恒定的温度。
白天,维恩和努玛在实验室里研发黑体,到了晚上,维恩继续待在实验室琢磨基尔霍夫那个能够预测黑体辐射的方程。1896年,维恩发现了他的公式,汉诺威大学的弗里德里希·帕邢(Friedrich Paschen:1865~1947)用其收集的黑体短波长能量数据证实了公式的准确性。
同年6月,维恩发表了自己这一关于能量辐射分布的定律,并同时也离开了PTR,在亚琛技术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in Aachen)谋了一个助教的位子。凭借他在黑体辐射上的这一发现,维恩最终于1911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当时他的离去却给努玛留下了繁重的工作,因为努玛需要做更多的测量,以在更高温度和更广范围内进一步验证维恩的公式。开始是与费迪南·考尔鲍姆(Ferdinand Kurlbaum:1857~1927)后来是与恩斯特·普林斯海姆(Ernst Pringsheim:1859~1917)合作,努玛花了两年时间,最终于1898年研发成功一种用电加热的黑体,这种设计方式极富艺术想象力。该黑体能够被加热到1500摄氏度,这是整个PTR花费十多年苦功才修得的成果。
努玛和普林斯海姆将测量的结果画在图上,其纵坐标为辐射的强度,横坐标为辐射的波长,他们发现随着波长增加,辐射强度逐渐上升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黑体辐射的能谱曲线看上去就像是海豚的背鳍。温度越高,辐射强度变化就越剧烈。另外,这一曲线还显示出随着温度的上升,峰值的波长向紫外线的方向移动。
1899年2月3日,努玛和普林斯海姆在德国物理协会的会议上报告了他们的结果。努玛对包括普朗克在内的与会的物理学家们宣布,他们的实测结果证实了维恩位移定律的正确性。但是,这一定律背后到底反映出什么呢?不清楚。尽管,在总体上,实测结果与理论值吻合较好,但是在频谱的红外区域存在误差。原因之一可能是实验误差,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做实验,看看更广范围的波长和温度下结果何如。
在三个月的时间中,帕邢对努玛和普林斯海姆实验中所没有覆盖的低温区域进行了测试,他发布的观测结果也证实了维恩定律的正确性。普朗克对此深感振奋,他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会议上宣读了帕邢的论文。维恩定律给普朗克留下的极深的印象。对普朗克而言,探寻黑体辐射的能谱分布背后所隐藏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寻找统治大自然的绝对真理,“因为我一直认为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探求自然的绝对真理,所以我有些急不可耐了”。
在维恩公布其位移定律后不久的1896年,普朗克从物理学中那些坚如磐石的基本理论出发,开始推导维恩定律。三年后的1899年5月,普朗克认为利用强大而权威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推导。尽管不断有实验物理学家提出正面或者反面证据,但其他学者对他的推导表示支持,并开始将维恩定律改称为“维恩--普朗克定律(Wien-Planck Law)”。普朗克对自己的工作信心百倍,他认为“即使这一定律有什么缺陷,它也能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吻合”。另外,他觉得非常有必要对这一揭示辐射能谱分布的定律进一步进行实验验证,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正是检验热力学第二定律有效性的好机会。接下来,他如愿以偿了。
1899年11月初,在进行了九个月的大范围观测和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实验误差以后,努玛和普林斯海姆发布了他们的结果:他们发现“在理论值和观测值之间存在着系统误差”。尽管在短波长领域,观测值与理论值完美匹配,但维恩定律所计算的长波长的辐射值显然过大。但是,仅仅过了数周,帕邢却对努玛和普林斯海姆的结果提出了异议,根据他所观测的另一套数据,他认为维恩定律“是一个非常正确有效的自然定律”。
当时,大部分顶尖学者都在柏林生活和工作,于是德国物理协会在首都召开的会议变成了大家进行学术讨论的论坛,而讨论的中心集中在黑体辐射与维恩定律。1900年2月2日,当努玛和普林斯海姆发布了他们的最新观测报告时,黑体辐射与维恩定律再一次成为物理协会的双周会上的统治性议题。他们发现在红外区域,观测值与维恩定律的预测值之间存在着系统误差,而这一误差无法用实验误差进行解释。
维恩定律的失败掀起了一股寻找替代定律的热潮。但这些临时性的替代公式被证明并不成功,人们迫切需要在更广的波长范围内进行观测从而能真正建立一个公式来解释维恩定律的误差。的确,在短波长范围内,维恩定律是有效的,但是努玛和普林斯海姆实验数据却证明该定律在其他波长范围是失效的,
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实验数据的基础上,普朗克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同时强烈认同“只有在不同的观测者所得到的观测值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才能考虑观测值与理论值之间是否冲突”。虽然如此,不同观测者所得到的结果尽管不能互相一致,他还是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理论是否存在什么不足。1900年9月末,当他正忙于修正自己的推导时,维恩定律在远红外区域失效的结论被证实。
一锤定音之人是普朗克的密友海恩里希·鲁本斯(Heinrich Rubens:1865~1922)和另一位德国物理学家斐迪南·库勒鲍姆(Ferdinand Kurlbaum:1857~1927)。当时,鲁本斯年满35岁,在位于柏林大街的技术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on Berliner Strasse)(即后来的“柏林工业大学”)任教,刚刚被提升为正教授,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附近的PTR做客座学者。也就是在PTR,鲁本斯和库勒鲍姆研制了他们的黑体模型,并凭借该模型能够测量红外线以外的未知区域。整个夏天,他们测量了波长为0.33毫米和0.66毫米之间、温度为200摄氏度至1500摄氏度之间的区域,来验证维恩定律的有效性。在这些长波长范围内,他们发现理论值与观测值之间的误差非常之大,这说明了一个事实---维恩定律不成立!
鲁本斯和库勒鲍姆想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上对德国物理学界公布他们的结果。可接踵而来的会议是在10月5日,这一天是星期五,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写论文。于是乎,他们决定还是等到两周以后的下一次会议上再说吧。但同时,鲁本斯知道普朗克一定急于得到这个消息。
格伦沃尔德(Grunewald)是位于西柏林郊区的一个富人区,这儿的住户大多是银行家、律师和一些教授,普朗克也是其中一员,他在一个带有大花园的大房子里住了五十年。十月七日,星期天,鲁本斯和妻子来普朗克家吃午饭。两位老朋友间的谈话不由自主就转到了物理学和黑体问题。鲁本斯解释了自己的最新观测结果,认为维恩定律不成立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维恩定律在长波长和高温条件下是失效的。普朗克得知,观测结果显示出在长波长范围,黑体辐射的强度与温度成正比。
那天晚上,普朗克决定着手构建一个能预测黑体辐射能谱的公式。现在,他有三方面的关键信息来帮助自己完成这项任务。首先,维恩定律被证实在短波长区域是有效的;其次,该定律在鲁本斯和库勒鲍姆所观测的红外区域是失败的,在此区域,辐射强度与温度成正比;第三,维恩定律中所观测到的“位移”现象是正确的。普朗克必须要把这三块黑体研究的拼图块儿组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公式。多年的科学研究,使普朗克很快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经验判断转化成草稿纸上面的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
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在灵光乍现的科学猜想和第六感觉相助之下,普朗克得到了他的公式。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难道它就是那个基尔霍夫孜孜以求的公式吗?在所有能谱范围内的给定温度下,它是否成立?普朗克迅速地写了一张便条给鲁本斯,然后大半夜就出门把便条邮寄出去。几天以后,鲁本斯带着答案来拜访普朗克了,他证实普朗克的公式与所有观测数据完全吻合!
10月19日,星期五,在德国物理协会的会议上,鲁本斯和普朗克坐在听众席上,库勒鲍姆首先做了发言,他郑重宣布维恩定律只有在短波长区域是有效的,在红外区域这样的长波长范围,则是不成立的。库勒鲍姆刚落座,普朗克就库勒鲍姆的发言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维恩频谱公式的改进(An improvement of Wien's Equation of Spectrum)”。他首先承认自己过去曾经认为“维恩定律肯定是正确的”,而且自己在以前的会议上曾经反复强调这一点。但接下来,普朗克所说的就并非什么简单的“改进”或者是对维恩公式的微调,而完全是一个新的属于普朗克自己的定律。
在进行了不到十分钟的论述之后,普朗克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公式。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同行们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宣布该公式“就目前来说,它与所有观测数据完全吻合,现在,该公式正式问世了”。当他坐下的时候,普朗克看见大家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但却默不作声。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普朗克刚才提出的公式不过是一个用来解释实验结果的临时性数学公式,而其他人也曾经提出自己的公式,来解释维恩定律在长波长区域的误差。
第二天,鲁本斯来看望并安慰普朗克。“他告诉我说,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他用我的公式与他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认真比对,”普朗克之后回忆说,“结果发现所有的数据点都匹配准确。”过了还不到一周,鲁本斯和库勒鲍姆宣布他们将自己的观测数据与五个公式的理论预测值进行了对比,发现普朗克的公式比其它任何一个都更加准确,帕邢也证实普朗克的公式与他的数据完全吻合。尽管实验物理学家们用自己的观测结果证实了普朗克的公式的准确性,但普朗克却遇到了麻烦。
他是有了自己的公式,可这个公式意味着什么呢?在它背后隐藏着什么物理涵义?如果普朗克不能给出一个答案,他明白自己的公式不过是对维恩公式的一个“改进”,“仅仅是由于灵光乍现获得了一个定律的地位”,“也就是一般意义而已”。“因此,从我发现这个公式的第一天起,”普朗克后来说,“我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寻找这一公式的真正物理意义的研究中去”。要想做到这一点,他只能从基本的物理定理开始一步步进行推导。普朗克已经知道了推导的结果,但他得找到一条通向终点的道路。虽然他已经有了一位身价不凡的向导,也就是公式本身,但是,为了这趟征程,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接下来的六周,普朗克后来回忆说,“是我一生中最勤奋的时候”,在那之后,“黑暗过去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天地出现了。”11月13日,他在写给维恩的信中说:“我的新公式还是很令人满意的;现在,我已经为它找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四周之后,我将于此地(即,柏林),在物理协会上向大家公布。”但普朗克对维恩只字未提自己是如何经过艰苦的脑力劳动创造出新的理论,也没有谈到理论本身的内容。在这些日子中,他一直锲而不舍地妄图将他的公式与十九世纪的两大物理理论(即,热力学和电磁学)联系起来。可是,他失败了。
“因此,要想发现一个新的理论必须要不惜任何代价,”他接受了失败的现实,“无论代价有多高”。他“已经做好准备,不惜推翻自己以前所信奉的每一条物理定律”。只要他能够“带来正面的结果”,他不再顾及自己要付出何种代价。普朗克是一个感情内敛的人,只有在弹奏钢琴时他才会尽情渲泄自己的情感,但这一次,他却说出感情如此强烈的话语来。为了透彻理解自己的新公式,普朗克将自己的脑力发挥到极致,他不得不做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动”,并最终发现了量子。
当对黑体内壁进行加热的时候,内壁会向黑体内腔释放出包括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在内的各种辐射。为了在理论上推导出黑体辐射公式,普朗克必须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物理模型,并还原出一模一样的黑体能谱分布。一直以来,他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想法。理论模型是否与观测值完全一致并不是最重要的;普朗克孜孜以求的只是该如何让自己的理论能够正确解释所有频率或者波长的黑体辐射。黑体辐射的能谱分布仅与温度相关,而与黑体本身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没有关联,这一现象是普朗克用来推导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
“尽管原子理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普朗克在1882年写道“但基于物质是连续的这一基本假设,原子理论终将被人们抛弃。”十八年之后,若干无可争议的证据已经证实了原子的存在,普朗克却依旧对此持反对态度。普朗克知道根据电磁理论,按照一定频率震荡的电荷仅在该频率才能释放或者吸收辐射能量。因此,他将黑体内壁假定为一个由无数振子组成的点阵。尽管每个振子都有自己的独有的频率,但总体上呢?该黑体所释放的辐射覆盖了所有频率范围。
摆锤就是一个振子,摆锤前后摇晃再回到其初始点为一次震荡过程,而一秒中摆锤震荡的次数就是其频率。另一种振子是一个悬垂于一根弹簧的重物,如果用力将重物从其静止点往下拉动再松开手,则重物会上下弹抖,每秒钟其上下弹抖的次数为其频率。在普朗克开展研究的时候,人们对这一类振子的物理原理已经理解得非常透彻,并将其命名为“简谐运动(Simple Harmonic Motion)”,普朗克在自己的理论模型中也用到了这一概念。
普朗克假定这个由无数振子组成的黑体,是一组具有不同刚度但质量为零的弹簧,每个弹簧都具有不同的频率,且都带有一个电荷。通过加热黑体的内壁,使这些振子有足够的能量进行运动。每个振子是否运动仅仅取决于温度。如果某个振子运动,则其在黑体内腔中会释放或者吸收辐射。假如,温度保持恒定,则振子与黑体内腔之间的辐射释放和吸收将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处于热平衡(Thermal Equilibrium)状态。
因为黑体辐射的能谱分布反映了所有能量在各个频率上的分布状态,普朗克假定这是因为在每一给定频率上的振子的数目决定了能量的分配。在设定了假想模型以后,普朗克必须要设计一种方案来将能量分配到每个振子上面。在公布了自己的黑体辐射公式后的几周中,普朗克为了构建出解释这一公式的物理理论,殆精竭智,苦苦探索。他发现如果依靠那些他一直奉为圭臬的已有的物理理论,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绝望中,他不得不借鉴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的理论,此人是原子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就这样,在探究黑体辐射公式的工作中,普朗克接受了原子并非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东西这一事实,尽管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公开场合“强烈反对原子理论”,但现在他成为了这一理论的皈依者。
路德维希·玻尔兹曼是收税官的儿子,身材粗短,留着一部带有浓重的十九世纪风格的大胡子。1844年2月20日,玻尔兹曼出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曾经跟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学过一段时间的钢琴,但显然,他更适合成为一位物理学家而不是一位钢琴家。1866年,玻尔兹曼在维也纳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没过多久,他就因为在气体运动学理论上作出的贡献而声名鹊起,该理论的命名是因为其支持者认为气体是由处于连续运动状态中的原子或者分子组成的。后来,在1884年,玻尔兹曼对其以前的导师约瑟夫·斯特凡(Joseph Stefan:1835~1893)的发现做出了理论论证,即认为黑体辐射的总能量与温度(注:本文中的温度如无特别说明,则为卡氏温度,即绝对温度)的四次方,即T4或者TxTxTxT,呈正比。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黑体的温度升高一倍,则其辐射的能量将增加16倍。
玻尔兹曼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和能干的实验物理学家,但他却是一个目光非常短浅的人。当时,只要欧洲任何一个顶尖大学出现了职位空缺,玻尔兹曼的名字通常就会出现在候选者的名单中。就是因为他拒绝了柏林大学因为基尔霍夫去世而留下的教授空缺,作为次级候选人的普朗克才有机会获得这一职位。1900年,频繁跳槽的玻尔兹曼在莱比锡大学任教,这时的他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但是,也有许多像普朗克这样的物理学家并不认同玻尔兹曼在热力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
玻尔兹曼认为气体的特性,比如压力,是由微观现象在动力学和概率论的定律支配下所表征出来的宏观特性。原子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每个气体分子的运动都是由经典牛顿力学支配的,但在实际上,想用牛顿运动定律来计算单个气体分子的运动状态那是根本做不到的。1860年,年仅28岁的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在并未测定单个分子速度的情况下探索出气体的运动规律。气体分子相互之间以及分子与容器壁之间不断发生碰撞,基于这一认识,麦克斯韦利用概率统计理论描绘出气体分子的速度分布规律。将概率统计方法引入到物理学领域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富有创新力的;通过这一方法,麦克斯韦能够成功解释人们所观测到的许多气体活动特性。玻尔兹曼比麦克斯韦年轻十三岁,他紧跟这位前辈的后尘,帮助发展和建立了气体运动学理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又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所做的是将熵与无序性联系起来,从而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统计学解释。
根据玻尔兹曼定理,熵可以用来度量某一系统处于某一特定状态的概率。例如,如果把一幅扑克牌洗得足够开,它就成为一个熵值很高的无序系统。但是,如果我们拿出一副新牌,则扑克牌是严格按照从A到王排序的,这副新牌就是一个高度规律性的低熵值系统。玻尔兹曼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反映了一个低概率低熵值的系统是如何向高概率高熵值状态演化的。但第二定律并非是绝对成立的,也有可能一个系统会从无序状态变成比较有序,例如把一副错乱无序的牌,再洗上第二次,就有可能会变成一副规则排序的牌。但这只是基于纸面上的,发生这种变化的几率非常之低,如果真要实现的话,估计所花费的时间将是宇宙年龄的若干倍。
普朗克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绝对成立的——熵只会增加。而根据玻尔兹曼的统计解释,熵值并不总是增加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熵在一定条件是可以减少的。很显然,两个人关于熵的认识存在差别。对普朗克而言,投向玻尔兹曼这一边意味着自己必须要作出放弃,而所要放弃的东西却是他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一直以来都极为珍视的。但是为了能推导出黑体辐射公式,他别无选择。“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熵和概率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对这种想法我也毫无兴趣,因为任何概率预测都允许特例的存在;当时,我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有效的,而且没有任何例外情况。”
最大熵以及最无序状态是一个系统最有可能出现的状态。对于黑体而言,这种状态即为热平衡状态,该状态也就是普朗克一直以来所研究的那些“振子”的频率最有可能的分布状态。如果总计有1000个振子,其中10个的频率为v,那么也就是这10个振子决定了该频率(v)的辐射强度。如果普朗克的电荷振子中的某一个的频率为一固定值时,则其释放或吸收的能量将仅仅取决于它的振幅,也就是其震荡的幅度。如果一个摆锤在5秒钟内完成5次摆动,则其频率为每秒一次摆动。然而,一个摆动幅度较大的摆锤要比摆幅小的摆锤具有更多的能量。摆锤的频率是由摆锤的长度决定的,由于摆锤的长度是一定的,则其摆动频率也是固定的,能量越高的摆锤摆动地更快一些,也能摆动更大的幅度。但是,由于它们的频率是相同的,则在相同的时间内,摆幅较大的摆锤摆动的次数与摆幅较小的摆锤是一样的。


利用玻尔兹曼的理论,普朗克发现自己能够推导出黑体辐射的公式,前提条件是这些振子所释放或吸收的能量与频率呈正比的。每个频率上的能量是由若干大小相等但不可见的“单位能量”(即量子)组成的,这一点是“整个计算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地方”,普朗克后来回忆说。
根据自己这个公式,普朗克被迫将能量E切分成若干能量为hv的单位能量块儿,其中,v为振子的频率,而h为一个常数。E=hv后来成为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方程之一。例如,如果频率v为20,而h为2,则每个量子的能量为20x2=40。如果在这个频率上有10个振子,其总体能量为3600,则3600/40=90,说明有90份量子的能量被分配在这10个振子身上。普朗克从玻尔兹曼那儿学习到如何计算这些振子中量子的最有可能的分布状态。
他还发现,这些振子所拥有的能量只能是0,hv,2hv,3hv,4hv,……,nhv,其中n为整数。也就是说无论是吸收还是释放的能量,其基本“单位能量”或者“量子”为hv。这就好比每次人们去取款机存取现金的时候,钞票的面值只能是1英镑,2英镑,5英镑,10英镑,20英镑和50英镑,因此从取款机中得到的钞票面值只能是这些单位面值的整数倍。因为普朗克的振子不拥有其它能量,则其震荡的幅度是限定的。这个理论看上去有些古怪,但我们可以考虑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拴有重物的弹簧进行类比。
如果该重物震荡的幅度为1cm,则设定其能量为1(此处,我们忽略能量测量单位)。如果该重物被拉坠到2cm,放开它以后,它就开始震荡,且其震荡频率保持不变;另外,其能量与振幅的平方呈正比,也就是说其能量现在为4。如果把普朗克对于单位能量的限制拿来约束该重物的震荡过程,则在1cm和2cm中间,允许存在的幅度只能是1.42cm和1.73cm,因为它们的能量分别为2和3。假如其振幅为1.5cm,则相应的能量为2.25,但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出现的。虽然人们无法直接观测到一份量子能量的大小,但是量子能量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一个振子所能接受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份单位能量,或者为零。这种理论显然与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物理常识背道而驰。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震荡的幅度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一个振子所能释放或者吸收的能量是没有限制的,这份能量可以是任意一个数值。
普朗克现在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但他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如此不可思议和出人意外,以至于他忽略了它们的真正意义。他的这些振子不能像水龙头里面的水一样,绵绵不断地吸收或者释放能量。与此相反,它们所获得或者失去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只能是单份出现的微乎其微分无可分的能量,即E=hv,其中v为振子的振动频率,在此频率上,振子可以吸收或者释放能量。
为什么人们无法观测到这些原子尺度的振子呢?因为h的值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26尔格·秒(erg seconds),即6.626除以10的27次方。根据普朗克的公式,能量增减的变化率不能小于h。h值是如此之微小,当用它来计算摆锤或者是那些振子的振动时,它所带来的量子效应在人们眼中的这个寻常世界是无法观测的。
普朗克的振子迫使他自己不得不把辐射能量斩成段,再切成丁,最后变成大小为hv的能量块。但在内心深处,普朗克并不认同能量是可以被切分成量子的。按照玻尔兹曼的切分方法,能量可以无限切分下去,直至在数学意义上无限接近于零(即无能量状态),但是整体能量却保持不变,这种方法让普朗克难以苟同。把这些能量块重新组合起来,则需要用到以微积分为主的数学方法。但普朗克的运气不是很好,如果他用上微积分的话,则他的公式就会化于无形。他似乎是卡在量子这个坎儿上了,但他并不在乎,因为他已经有了公式,剩下来要做的事情不过是把公式解释清楚,而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柏林大学物理学院的教室里,普朗克向德国物理协会的会员们问候道:“先生们!”。在台下的听众中,他能够看见鲁本斯、努玛和普林斯海姆。他的报告题目是“Zur Theorie des Gesetzes der Energieverteilung im Normalspektrum(关于普通频谱的能量分布定理之理论依据)”。这一天是1900年12月14日下午5点刚过。“几周以前,我有幸向诸位介绍了一个新公式,这个公式能够在准确解释一般频谱范围内的能量分布规律。”接下来,普朗克阐述了他在推导这一公式过程中所发现的其背后隐藏的物理涵义。
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同行们对他报以热烈的祝贺。在介绍量子的概念时,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个能量块“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而且他自己“并不真的赞同这个想法”,那一天其他人也抱有相似的观点。但是,对大家最重要的一点是,普朗克对他在十月份所提出的公式给出了一个有物理意义的解释。的确,他那种把能量切分成量子的想法有些稀奇古怪,但这个理论会在未来得到逐步完善。所有的人都认为普朗克的理论不过是理论物理学家经常玩的一个魔术,即在找寻正确答案的过程中用一些数学技巧,但它并不代表什么真正的物理涵义。在这之后,让他的同行感到振奋的是普朗克的辐射公式与观测结果精确吻合;但同时,没人真正注意到能量子(Quantum of Energy)这一概念,包括普朗克自己。
一天早晨,普朗克和他七岁的儿子埃尔文(Erwin)一同离家出门,这对父子是去附近的格伦沃尔德森林散步。普朗克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在森林里漫步,而且他喜欢携子同行。埃尔文后来回忆说他们边走边聊,父亲对他说:“今天,我有了一个可以和牛顿比肩的重大发现”。多年以后,再回忆起那一幕的时候,埃尔文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天他和父亲进行的这次散步,大概是普朗克进行十二月的那次学术报告前的某一天。有没有可能那天普朗克完全认识到量子的伟大意义?或者他只是试图向自己的儿子显摆一下他的新辐射公式是如何重要?这两种猜测都不正确。普朗克如此兴奋只是因为他发现了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基本常数,k和h,前者被他称为“玻尔兹曼常数(Boltzmann's Constant)”,后者被他称作是“动量子(Quantum of Action)”,后来被其他物理学家命名为“普朗克常数(Plunck's Constant)”。这两个数都是固定的永恒的,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绝对常数。
普朗克认为自己欠玻尔兹曼一份人情,因此当他在推导黑体辐射公式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常数时,他用这位奥地利物理学家来命名这个数。另外,普朗克还先后在1905年和1906年提名玻尔兹曼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这一天来得有些迟了,玻尔兹曼长期以来疾病缠身,他患有哮喘,偏头痛,视力衰退和心绞痛等多种疾病,但真正困扰玻尔兹曼的是严重的抑郁症。1906年九月,在意大利里雅斯特(Trieste)省的杜伊诺(Duino)休假期间,玻尔兹曼上吊自杀。那一年,他62岁。尽管玻尔兹曼的朋友们一直以来就担心什么时候会突然听到他的死讯,但当这个最坏的消息真的到来的时候,朋友们无不感到震惊。玻尔兹曼总觉得自己被大家孤立,也没有人欣赏他的学识。可事实是这样的吗?玻尔兹曼是那个时代声名最为卓著且受众人敬仰的物理学家之一。但是,由于在原子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上,玻尔兹曼和别的学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结果让他心力交瘁,觉得自己一生的成果正一步步被人打入冷宫。1902年,玻尔兹曼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到维也纳大学。玻尔兹曼死后,维也纳大学向普朗克发出邀请,希望能由他来继承玻尔兹曼的衣钵。尽管普朗克认为玻尔兹曼的工作是“理论研究中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而且他也确实对维也纳大学所许诺的优厚待遇怦然心动,但他还是婉拒了这个邀请。
常数h好比是一把利斧,可以将能量切割成量子,普朗克就是锻造这把斧头的第一人。但是,普朗克只是将那些假想的振子释放或者吸收能量的过程量子化。普朗克并没有量子化,或者说将能量本身切割成大小为hv的能量块。毕竟,发现一个新事物和弄清这一新事物的原理是两码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过渡时期。普朗克本应发现的东西依旧隐藏在他的推导过程中,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本来应该将振子做量子化,进行单个考虑,但他并没有明确地这么做,而是将这些振子当做一个整体考虑。
普朗克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他认为自己可以消除掉量子,等他意识到自己这个错误时他已经走出很远了。普朗克的保守是深入骨髓的,其后果是他试图将量子融入到现有的物理体系中去,这种无用功白白耗去了他的大好时光。他也知道有些同行认为他的工作不过是自寻死路。“但我并不这么看。”普朗克后来写道:“我现在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h这一基本量子常数在物理学中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我起初居然对此心存疑虑。”
1947年,普朗克病逝,享年89岁。又过了数年,普朗克以前的学生和他的同事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曾经回忆说普朗克为了“避开量子理论,或将量子理论的影响降到最低点”而进行了绝望的挣扎。弗兰克很清楚,普朗克“是一个与自己的本心做抗争的革命者”,他“最终得出了结论——‘我以前做的是无用功。我们必须和量子理论共处一室。请相信我,这一理论会得到发展的。’”这段话是一段恰如其分的墓志铭,正适合这位欲拒还迎的革命者。
物理学家的确不得不和量子“共处一室”。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是普朗克那些名声显赫的同行,而是一位居住在瑞士伯尔尼(Bern)的年轻人,只有他一个人认识到量子的革命性意义。这位年轻人并不是一位职业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初级公务员,普朗克认为他就是第一个发现能量本身是量子化的那个人,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第一章完)
瑞士伯尔尼,星期五,1905年3月17日。时针正指向早上8点,一位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显得有些古怪的格子西装,手上抓着一个信封,脚步匆匆地走在上班路上。路人会发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绣着花边的绿拖鞋,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爱因斯坦一家住在一个狭小逼仄的二居室公寓里,这儿位于伯尔尼风景如画的老城区中。每周六天,在这个时间,他会向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告别,接着走上十分钟左右,最后到达一栋庞大的砂岩建筑。该建筑所在的杂货街(Kramgasse)是伯尔尼市最美的街道之一,街上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漂亮钟塔(Zeitglockenturm),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两侧是美丽的拱廊。爱因斯坦朝这栋联邦邮电局(Federal Post and Telephone Service)的总部大楼走去,他还沉浸在思考中,因此对周边的世界视若无睹。一进楼,他径直走向楼梯,上到三楼,这儿是联邦知识产权局(Federel Off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也就是著名的“瑞士专利局(Swiss Patent Office)”的办公室。在这里,爱因斯坦和其他几十位技术专家,坐在办公桌边,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处理一大堆漏洞百出荒诞可笑的专利申请,从矮子里面拔几个将军。
三天前,爱因斯坦刚刚庆祝了他的二十六岁生日。正如他之后回忆说,整整三年,他一直就是“专利的奴仆”。对他而言,这份工作意味着他不用担心会“饿肚子”。爱因斯坦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工作的内容充满着变数,而且能唤起很多“奇思妙想”,另外,办公室的工作气氛让人感到很放松,爱因斯坦后来把这儿称为“俗世的修道院”。尽管三级技术专家这项工作是一个很低微的职位,但是薪酬还是很不错的,而且爱因斯坦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爱因斯坦的顶头上司是哈勒尔先生(Haller),性格严厉,老喜欢盯着爱因斯坦,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在处理专利申请的工作之余,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偷偷做计算,以至于他把自己的办公桌变成了“理论物理的办公室”。
普朗克有关黑体研究的论文发表后不久,爱因斯坦就阅读了它,他后来在谈到自己当时的感受时回忆说:“就好比我们把地层翻了个底朝天,地基都不牢靠,而我们却要在上面盖房子。”爱因斯坦往信封中塞了一篇论文,他准备将其投寄到《物理年鉴》(Annalen der Physik)这一顶级物理学术期刊,而这篇在1905年三月寄送的论文意义深远,甚至远远超过普朗克引入量子理论这一功绩。爱因斯坦明白,自己所提出的光量子理论在当时不啻于是一种异端邪说。
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的五月中旬,爱因斯坦在写给自己的好友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说,他希望能投寄出四篇论文,并在年底之前看到它们被发表出来。其中,第一篇就是关于量子的论文;第二篇是他的博士论文,在文中他提出了一种测定原子大小的新方法;第三篇则对布朗运动(即液体中的细微悬浮颗粒,比如花粉,所呈现的随机运动现象)做出了解释;“第四篇论文”爱因斯坦说“只是给出了一个粗略的方案,关于移动物体的电动力学,我做了一些空间和时间方面的理论修正”。爱因斯坦在1905年所发布的这一系列论文是如此非同寻常,在科学发展史上面,能在一年之内完成如此多的重量级伟大发现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1666年的艾萨克·牛顿。这一年之中,这位年仅23岁的英格兰小伙子奠定了微积分的理论基础,建立了重力理论,还开创了光学。
爱因斯坦在他所发表的第四篇论文中首次勾勒出一个伟大的理论——相对论(Relativity),而他自己也即将成为这一理论的代名词。尽管相对论将彻底改变人类对时间和空间本质的理解,爱因斯坦却认为,“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是自己在普朗克的量子概念上发展出来的光量子理论,而非相对论。爱因斯坦指出,相对论其实只是对牛顿和其他前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做了“修正”,但他提出的光量子概念则是一个全新的且只属于他自己的发现,它意味着突破了以前的物理学体系。对这样一位业余物理学家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亵渎。
在当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光是一种波动现象。在“对光的产生及变化的一种探索(On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 Concerning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ght)”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提出光并不是由波组成的,其基本组成单位是像粒子一样的量子。在普朗克对黑体问题进行分析时,他很勉强地引入的观点是:能量是以量子的形式,被一份一份地吸收或者释放出来。但是普朗克自己,正如其他众人一样,认为电磁辐射在与物质发生接触时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能量交换,它本身只是一种波动现象,爱因斯坦革命性的“观点”则认为:光(,实际上所有的电磁辐射)都不是波,而是能够被切分成微小的能量块儿,也就是光量子。在这之后的二十年中,至少在公开场合,除了爱因斯坦自己,没有任何人接受光量子的概念。
从一开始,爱因斯坦就知道想让自己的光量子理论能够被大家认可,其难度不亚于攀登高山。这也是他之所以在自己的论文标题中加上“对......的一种探索(On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这几个字。根据《简编牛津英语词典(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Heuristic”被解释为“为得到结果提供服务(serving to find out)”。当物理学家们在解释光辐射现象问题正束手无策之际,爱因斯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方法,但这一方法并不是从基本定律出发的。在建立量子理论体系的道路上,爱因斯坦的论文是一个方向标,但对于那些尚没有做好准备向此方向前进的旅人们而言,这个标志的意义有限,因为其指向与大家长期以来所认可的光是一种波动现象的理论背道而驰。
在1905年3月18日至6月30日之间,《物理年鉴》先后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四篇论文,这些论文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为物理学体系引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年中,爱因斯坦还抽出精力和时间为该学术期刊写了21篇书评。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他事先并没有告诉哈比希特,那就是他还写了第五篇论文。这篇文章中,他给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公式——E=mc2。在1905年春夏时节的伯尔尼,爱因斯坦完成了他那一系列意义非凡的论文,事后,他回忆当时一波波灵感蜂拥而至,他说“在我心中,就像暴风雨冲破了桎梏”。
马克斯·普朗克当时是《物理通报》的理论物理学顾问,他是第一批阅读“关于移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特征(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这篇论文的人士之一。这一理论在第一时间就征服了普朗克,将该理论命名为“相对论”的人正是普朗克,而非爱因斯坦。对于光量子理论,尽管普朗克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但是他依旧为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的发表发放了通行证。此刻,他肯定产生过一丝疑虑,这位物理学家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写出如此非同凡响而又离经叛道的论文?
乌尔姆(Ulm)是一座位于德国西南角落的城市,多瑙河(Danube)穿城而过。中世纪的时候,在乌尔姆有一个非同凡响的格言——“乌尔姆人都是数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出生在这儿。1879年3月14日,在乌尔姆诞生的这个孩子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天才。男孩的后脑勺又大又歪,以至于母亲有些担心她刚生下的这个孩子可能被挤坏了。男孩很长时间不会说话,他的父母曾经担忧他可能是个哑巴。1881年11月,爱因斯坦家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玛雅(Maja)出生了。在妹妹出世后不多久,爱因斯坦开始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说话,他先是轻声重复他想说的句子,一直到自己能够不打磕巴为止,然后大声地将这句话讲出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岁,爱因斯坦才能在他的父母赫尔曼(Hermann)和波林(Pauline)面前正常说话。为了和自己的弟弟雅可比(Jacob)合伙做电器生意,赫尔曼已经举家迁居到了慕尼黑,那时,他们一家在那儿已经居住了六年。
1885年10月,慕尼黑的最后一所犹太人学校已经在十多年前就关闭了,六岁的爱因斯坦只能被送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去读书。在有着浓厚天主教传统的德国内地,宗教教育在学校课程中自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老师们“崇尚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任何信仰歧视”。虽然老师们崇尚自由主义,而且为人随和,但是反犹主义早已经深入到德国社会的骨髓中,时常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下,当然也包括在课堂上。爱因斯坦永远无法忘记在一堂课上,宗教课老师告诉学生们犹太人如何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爱因斯坦回忆说“孩子们中间,尤其是在小学里,反犹主义的阴影无处不在。”爱因斯坦因此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我确实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无论是对于我的祖国,还是对于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是对于我的最为亲近的家人,我从未有过真正的归属感。”爱因斯坦在1930年这么写到。他把自己称作是一辆单驾马车(Einspanner),也就是单匹马拉的马车。
在学校里,爱因斯坦喜欢个人挑战,而他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用扑克牌搭房子。尽管他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但凭着超乎寻常的耐性和韧劲,他能搭出十四层高的房子来。这些小事,反映出他已经具有一些基本的特质,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为什么在他人纷纷放弃的时候,爱因斯坦却能够独自在自己的科研道路上跋涉。“上帝赐给我的礼物,就是让我像骡子一样倔犟,”爱因斯坦说“和敏锐的嗅觉。”也许别人并不同意,但爱因斯坦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天份,只是特别有好奇心而已。很多人都有好奇心,但爱因斯坦所具有的好奇心一旦与他的倔犟个性相结合,那就意味着在别人都已经放弃发问的一些似乎有些孩子气的问题时,他却能坚持不懈追寻问题的答案。例如,如果骑在一束光束上面,那将会怎么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爱因斯坦花了十年之功创立了相对论的理论。
1888年,九岁的爱因斯坦进入吕特博特中学(Luitpold Gymnasium)读书,那段岁月在他的回忆中是非常苦涩的。马克斯·普朗克在少年时期所入读的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和死记硬背式的教学方法,可普朗克却如鱼得水,但在同样的环境下,爱因斯坦却很痛苦。尽管他痛恨那些老师和他们死板的教学方式,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偏重人文学科,但爱因斯坦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他的拉丁文获得了最高分,希腊文成绩也很棒,以至于老师评价说他是“无以伦比的”。
回到家后,爱因斯坦还得上音乐课,家教老师们所用的教学方式与学校里如出一辙,同样的机械僵化。但是,一位来自波兰的医学院学生给爱因斯坦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无价的。当时,马克斯·塔木德(Max Talmud)是21岁,爱因斯坦10岁。根据犹太教在安息日(Sabbath)要邀请贫穷的宗教学者吃饭的古老传统,每周四,塔木德会受邀到爱因斯坦家吃晚饭。塔木德很快就发现他和这个充满着好奇心的男孩有着相同的志趣爱好。没过多久,两个人就经常几个小时地泡在一起,讨论塔木德带来的或者推荐的书籍。他们开始只是讨论一些科普书籍,后来他们沉迷在“青年人的宗教天堂(Religious Paradise of Youth)”。
天主教学校中所受的教育,加上一位亲戚兼家教老师传授给他的犹太教教义,二者显然在爱因斯坦身上打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他的父母是很世俗化的人,可让他们吃惊的是,自己的儿子居然陷入到“狂热的宗教笃信”中。爱因斯坦不再吃猪肉,每天在上学的路上他会唱起圣歌,并且坚信圣经中关于创世纪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后来,在爱因斯坦贪婪地阅读完一本又一本科学图书以后,他开始意识到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些“胡思乱想加上国家有意灌输给他的那些谎言,以及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通通被他抛弃了。就这样,一颗质疑一切权威的种子被种在他的心灵中,并将陪伴他终身。他逐渐认识到尽管他的“宗教天堂”垮塌了,但是他却第一次把自己从“‘纯粹的个人世界’以及那些仅仅由愿望、希望和原始感官所统治的(感性)世界”中解放出来。
当爱因斯坦对宗教教义丧失兴趣的时候,他开始沉迷于一本几何小册子。在他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雅可比叔叔就曾经给他讲过基本代数,还给他布置数学题做。塔木德给爱因斯坦带了一本欧几里德几何的小册子,年仅12岁的爱因斯坦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的同龄孩子。让塔木德感到惊讶的是,爱因斯坦通过证明公式和做习题,异常迅速地就读完了本小册子。在那个暑假,他是如此热忱地学习着数学,以至于到了开学的时候,他已经提前掌握了那些应该在课堂里学习的数学知识。
爱因斯坦的父亲和叔叔都在电器工业领域工作,这个便利条件使得他不但可以通过阅读学习科学知识,还能够亲身了解如何运用这些科学技术去制造电器。正是他的父亲在无意中将爱因斯坦引领到科学的王国。一天,爱因斯坦发着高烧,正躺在床上,他的父亲赫尔曼给他带来一个罗盘。旋转的指针是如此的神奇,那时才五岁的爱因斯坦一想到“这个东西后面肯定还深深地隐藏着什么”,就激动得浑身发抖。
父亲和叔叔所开办的电器生意在起步阶段还是很兴盛的,他们生产电器设备,也修建电力和照明线路,从而掘得了第一桶金。爱因斯坦兄弟在生意场上一番风顺,甚至还获得了首次为慕尼黑啤酒节(Oktoberfest)提供电力照明的合同,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兄弟俩的公司在与西门子(Simens)和德国电器公司(AEG)的竞争中,最终渐处下风。当时,在这两个巨无霸的阴影下,很多小公司依旧欣欣向荣,并生存下来。但是,雅可比野心勃勃,而赫尔曼却是优柔寡断,因此他们无法成为那些委屈求全的幸存者之一。尽管在竞争中被击败了,但兄弟俩不愿意屈服,他们决定把生意转移到意大利去,在那儿,电器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正是一块可以东山再起的地方。1894年6月,爱因斯坦兄弟公司迁移到米兰,随同迁居的还有他们的家人,只有小爱因斯坦被留了下来,一位远亲负责照顾他,因为爱因斯坦还要在这个让他恨之入骨的学校里完成所剩下的三年学业。
为了让父母放心,他假装在慕尼黑事事顺心。但是,一想到强制性的兵役义务,他就越来越忐忑不安。根据德国法律,如果在17岁生日之前,他依旧在这个国家生活,那么一到年龄,他就必须去服役,否则他就会被视为一个叛国者。无依无靠、心情郁闷的爱因斯坦必须要想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突然,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了。
迪根哈特博士(Dr. Degenhart)是学校的希腊文老师,他曾经认为爱因斯坦会一事无成,但现在却成为他的人生导师。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中,迪根哈特博士建议爱因斯坦应该离开这所学校。有了老师的支持,他不再有所顾虑。爱因斯坦弄到了一份医疗诊断书,上面写着他身体有恙,需要充分的休息才能恢复元气。同时,爱因斯坦又从数学老师那儿弄来一纸证明,说明他已经精通数学,完全达到毕业标准。就这样,在爱因斯坦的家人离开慕尼黑以后仅仅过了六个月,他也接踵而至,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来到了意大利。
爱因斯坦的父母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但是他坚决拒绝返回慕尼黑,而且他已经有了替代计划,那就是待在米兰,为了在十月份踏进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Federal Polytechnikum in Zurich),认真准备入学考试。该学院成立于1854年,后来在1911年更改校名,这就是世界著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idgen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即ETH)。在当时,该学院并不是德语区的顶尖大学,非中学毕业生也可以进入这座大学。因此,爱因斯坦向他的父母解释说,他只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就能进入这座大学。
很快,爱因斯坦的父母就发现儿子的计划还有第二部分——他想放弃德国国籍,这样就不会被德意志帝国征召去服兵役。但是,爱因斯坦年纪太小,无法自己做这件事,他需要获得父亲的同意。赫尔曼最后答应帮这个忙,他向政府申请取消爱因斯坦的德国国籍。1896年一月,在花了三个德国马克之后,他收到一份正式的官方通知:他的儿子爱因斯坦从此不再拥有德国公民身份。在当了五年的法律意义上的无国籍人士以后,爱因斯坦成为瑞士公民。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他一直因坚持和平主义而闻名,但在1901年3月,即在他22岁之前,为了成为一名瑞士公民,根据法律规定,他必须要接受医疗检查并去服兵役。幸运的是,因为平足和静脉曲张,爱因斯坦未达到服役标准。当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度过他的少年时光时,真正让他犯愁的并不是服兵役这件事本身,而是他痛恨军国主义盛行的德国,不愿意为了维护这个帝国的利益而去穿上一身灰皮。
“虽然我在意大利仅仅逗留了几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当爱因斯坦在50年之后回忆起这段无忧无虑的岁月时,依旧让他回味无穷。他协助父亲和叔叔开展电器生意,还四处周游,寻亲访友。1895年的春天,爱因斯坦一家搬迁到米兰以南的帕维亚(Pavia)。在这儿,爱因斯坦的父亲和叔叔又开办了一家新工厂,但不幸的是,工厂只维持了一年多一点儿就再次倒闭。尽管碰上了这种变故,爱因斯坦还是认真准备了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可是他却失败了。由于爱因斯坦的数学和物理成绩非常出色,因此物理学教授特意邀请他来听课。这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邀请,但是爱因斯坦却听从了更为中肯的建议。他在语言、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绩很糟糕,理工学院的教务长要求他返回中学再去学习一年,而且给他推荐了一所瑞士中学。
十月底的时候,爱因斯坦来到了位于苏黎世以西30英里的阿劳(Aarau)。阿劳州立中学的学风比较自由,生机勃勃的氛围让爱因斯坦如鱼得水。读书期间,爱因斯坦寄宿在古典文学老师的家里,这段生活让爱因斯坦永生难忘。老师乔斯特·温特勒(Jost Winteler)和他的妻子波林(Pauline)养育有三个女儿和四个儿子,他们鼓励孩子们自由思考,每天的晚餐因此总是吵吵嚷嚷但却热热闹闹。没过多久,爱因斯坦就把温特勒夫妇当自己的父母看待,他称呼他们为“温特勒爸爸”和“温特勒妈妈”。尽管暮年的爱因斯坦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但青少年时期的爱因斯坦显然是需要人来关爱自己,而他自己也需要关爱他人。很快,1896年的九月到了,又到了入学考试的时间,爱因斯坦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踏上了去往苏黎世和理工学院的道路。